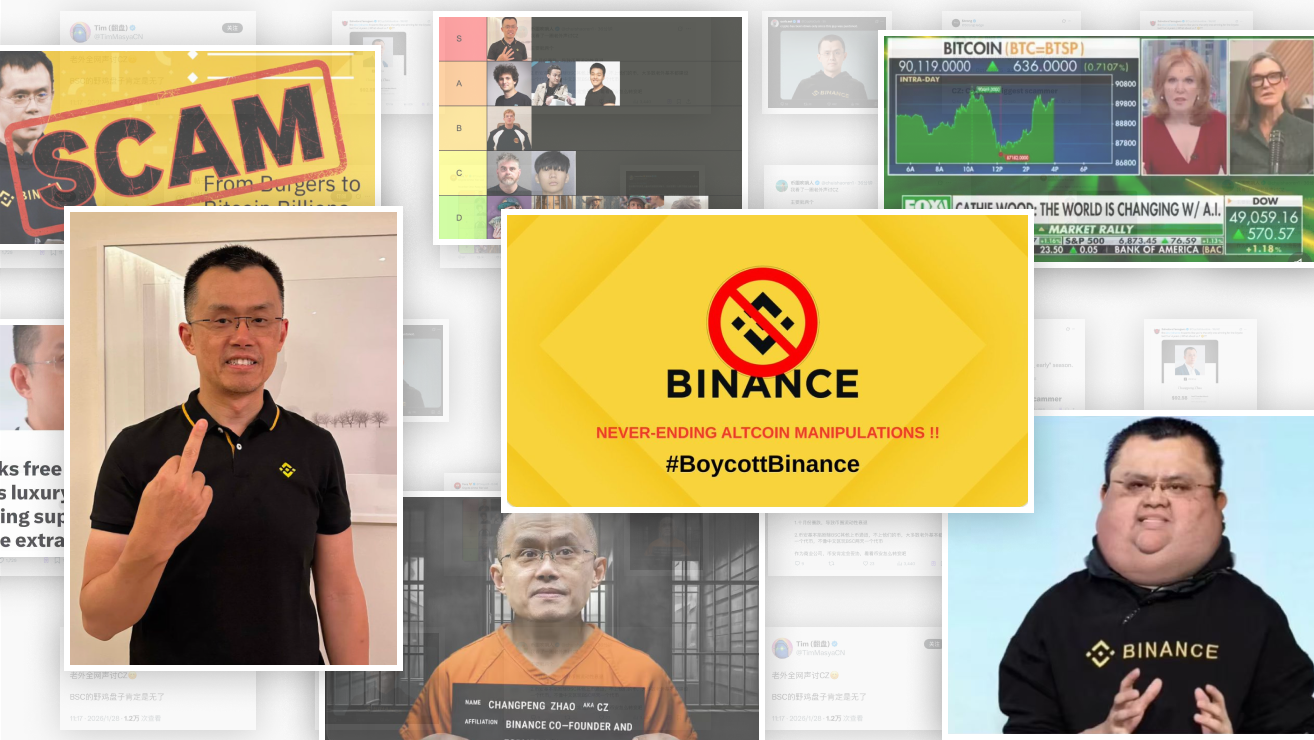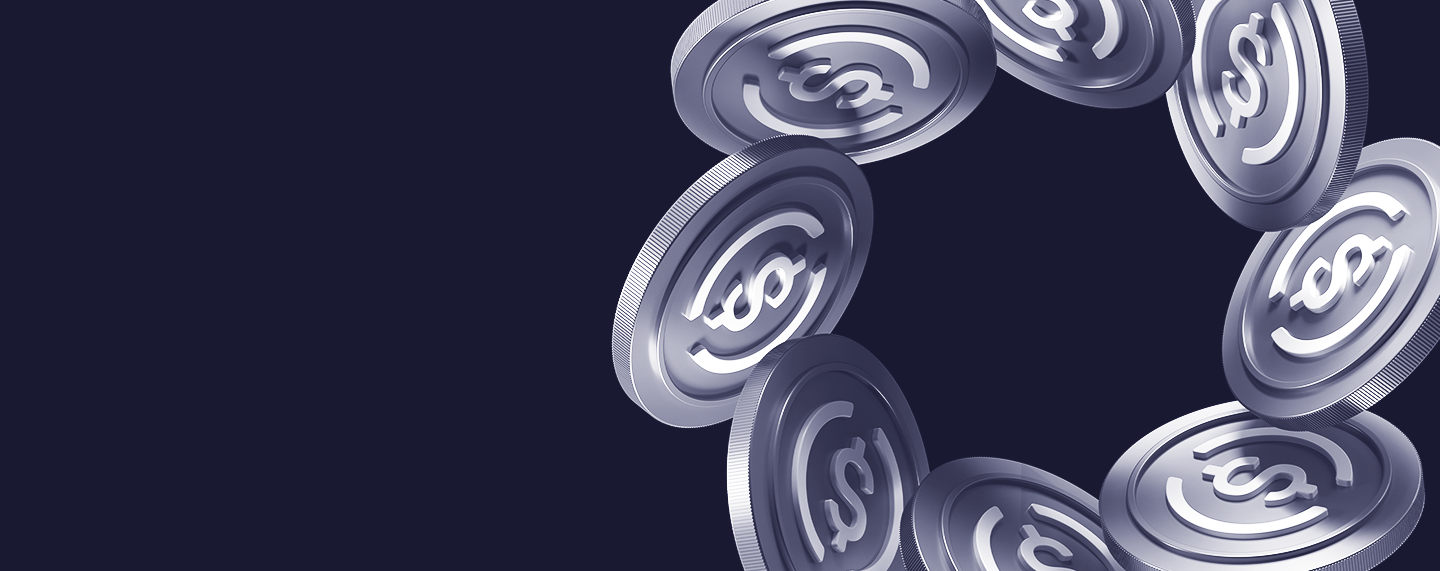CZ 特赦後首度深談:關於 40 億罰金、自由代價與“不能說的秘密”
TechFlow Selected深潮精選

CZ 特赦後首度深談:關於 40 億罰金、自由代價與“不能說的秘密”
CZ 坦言,一旦財富達到一定程度,金錢就只是一條線,不再能帶來更多快樂。
整理 & 編譯:深潮 TechFlow

嘉賓:CZ
主持人:Chamath Palihapitiya
播客源:All-In Podcast
原標題:Binance CEO:4 Months in Prison, $4 Billion Fine, and What Comes Next
播出日期:2026 年 2 月 10 日
要點總結
4 個月監禁、40 億美元罰款,這筆加密史上最昂貴的學費,讓 CZ 換來了一個重新審視世界的視角。
在本期播客中,Binance 創始人 CZ 首次公開談及他從普通移民孩子到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創始人的心路歷程。他不再避諱那些敏感的褶皺:被限制出境的滯留生活、獄警冷冰冰的“幫派建議”、以及與 SBF 決裂的真實始末。從麥當勞打工到辭去 Binance CEO 職位,CZ 分享了他的成長故事、職業生涯轉折點,以及對加密貨幣行業未來的洞察——一個不發幣的教育帝國 Giggle Academy,以及由 AI 智能體主導的下一代支付願景。
深潮 TechFlow 整理了這場歷時兩小時的對話,試圖帶你穿透千億身價的迷霧。
精彩觀點摘要:CZ 歸來後的五個“自白”
1.關於鐵窗生活:恐懼、誤解與“奢侈”的自由
外界對 CZ 的獄中生活充滿獵奇想象,但他坦承了真實的恐懼與荒誕的經歷。
- 恐懼勒索與“幫派”烏龍: CZ 坦言,判決後媒體大肆渲染他是“史上最富有的囚犯”,這讓他極度擔心自己會成為獄中勒索的目標。入獄第一天,獄警曾建議他“加入太平洋島民幫派尋求保護”,這讓他一度非常恐慌。但後來發現這只是因為亞裔面孔稀缺,被分到了一個僅有 6 個人的少數族裔小組,並未遭受霸凌。
- 重新定義“奢侈”: 自由的滋味體現在最微小的細節上。CZ 回憶道,獄中的淋浴間狹窄如盒,轉身都會碰到牆壁。出獄後他感到最奢侈的享受,竟然是“在一個寬敞的、不用碰到牆壁的淋浴間裡洗澡”以及“看到一盤新鮮水果”。
- 離開的 26 分鐘: 獲釋當天,從走出監獄大門到登上飛離美國的飛機,整個過程僅用了 26 分鐘。
2.關於監管博弈:心理戰、手銬照與被迫放手
揭秘 40 億美元罰單背後的談判細節,以及作為創始人最艱難的妥協。
- 司法部的“心理戰”: 談判過程被 CZ 形容為“煉獄”。他透露 DOJ(司法部)擅長使用“沉默戰術”——在拒絕條件後保持兩週的死寂,利用這段時間擊潰對手的心理防線 。他認為對方非常清楚,“兩週是最佳施壓時間”。
- 未遂的“手銬擺拍”: 雖然法官判定無需監管,但 DOJ 曾強烈要求當場給他戴上手銬帶走。CZ 懷疑這純粹是為了拍一張他被捕的照片用於宣傳,好在法官駁回了這一要求。
- 含淚辭任 CEO: 辭去 Binance 管理職並非主動選擇,而是認罪協議的一部分。CZ 承認這是最艱難的決定,當時甚至落淚 。但他意識到,只有放手,Binance 才能在反加密貨幣的監管環境下生存下去。
3.關於 SBF 與 FTX:拒絕背鍋,還原恩怨
針對“幣安搞垮 FTX”的陰謀論,CZ 進行了正面澄清。
- 早已退場: CZ 強調,幣安早在 FTX 崩盤前一年半(2021 年 7 月)就已完全退出股權,並不知道其內部財務狀況。
- “他想在這個行業裡殺死我們”: CZ 透露了與 SBF 決裂的細節:即便幣安曾是 FTX 的股東,SBF 仍在華盛頓政界背後詆譭幣安,甚至用 5 倍薪水挖角幣安的 VIP 客戶經理 。CZ 直言 SBF 是在利用監管攻擊競爭對手。
4.關於未來賽道:AI 智能體將重塑加密支付
卸任後的 CZ 將目光投向了更長遠的未來,這也是本次訪談中最大的 Alpha(財富密碼)。
- AI Agent 是最大的加密用戶: CZ 提出了一個極具前瞻性的觀點:未來每個人後臺將有成百上千個 AI 智能體(Agents)工作。這些 AI 無法在傳統銀行開戶(無法通過 KYC),因此它們註定只能使用加密貨幣進行價值交換。
- AI 交易量的爆發: 他預測,未來鏈上的高頻交易和資金轉移,絕大部分將由 AI 智能體完成,其頻率和規模將遠超人類。
- Giggle Academy 絕不發幣: 對於他的新教育項目,CZ 斬釘截鐵地表示“不會發行代幣”。他認為一旦引入代幣激勵(Learn-to-Earn),用戶就會變成“薅羊毛的礦工”,從而背離教育的初衷。
4.關於財富與人生:漏水的屋頂與“普通人”
剝離“首富”標籤,還原一個生活低調、追求內心平靜的 CZ。
- “漏水屋頂”的隱喻: 儘管身家千億,CZ 透露自己住的房子是“三四手舊房”,客廳屋頂每隔一個月就會漏水,但他並不在意,認為“只要功能夠用就好”。
- 金錢只是“一條線”: 他坦言,一旦財富達到一定程度(對他來說是在 2018 年登上福布斯封面後),金錢就只是一條線,不再能帶來更多快樂。
- 當下的滿足: 相比於管理萬億帝國的壓力,CZ 現在更享受不用每天開 20 個會議的生活 。他認為真正的成功不是成為天才,而是堅持做自己喜歡的事,並擁有好運氣。
從中國到加拿大
Chamath:CZ,歡迎來到《All In Podcast》,我想從頭聊起,讓我感興趣的一點是,你在加拿大的早期經歷和我有些相似,你曾在麥當勞打工,而我則在漢堡王工作過。不過在那之前,你的父母是從中國移民到加拿大的,對吧?
CZ:
我父親其實早在 1984 年就去加拿大學習了,他在中國是一名教授,後來參加了多倫多大學的一個交流項目,幾年後他去了溫哥華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UBC)。我們那時也在申請移民,但拿護照非常困難。我們大概在 1985 年開始申請,花了兩三年才拿到護照,然後又花了幾年時間才拿到簽證。
在後來就不再輕易發放新的護照了,重新申請護照變得更難。但我們很幸運,在事件發生前一年拿到了護照,之後簽證反而更容易了,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件事反而幫助了我們獲得簽證。
Chamath:你們一家團聚後,父母都工作了嗎?他們做什麼工作?
CZ:
我父親繼續在大學當助理教授,每月有 1000 加元的生活津貼。我們還住在 UBC 提供的低租金教職員工宿舍裡,所以住在校園裡。我記得我們到加拿大的第三天,我媽媽就去了一家縫紉廠工作,做衣服。她在中國是數學和歷史老師,但因為英語不好,沒法找到相應的工作,只能去工廠打工,拿最低工資。她在工廠工作了七到十年。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麥當勞,我記得當時是 14 歲還是 15 歲,當時的最低工資是 6 加元,不過麥當勞只付 4.5 加元,這比最低工資還低。因為他們似乎有某種特殊豁免,允許僱傭很多年輕人。我記得我在 14 歲生日那天申請了這份工作,一週後就開始在那裡翻漢堡了,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份收入。
CZ 的普通早期職業生涯
Chamath:你並不是那種天才型技術少年,整天埋頭編程、學習計算機科學的那種人,對吧?
CZ:
我不會這麼形容自己,我覺得自己算是個技術型的人吧。我學的是計算機科學,高中時就對編程感興趣,也學過一些編程。不過我並不是那種天才程序員,也不是特別厲害的那種。我覺得自己算是個不錯的程序員,職業生涯中也寫過一些還可以的代碼。但到了 28 歲到 30 歲左右,我開始慢慢遠離編程,更多地從事商業開發、銷售等工作,大概有 8 年的時間,我主要做這些事情。
Chamath:所以你其實就是一個普通的移民孩子,努力適應加拿大的生活。那你有很多朋友嗎?
CZ:
我有很多朋友,既有亞洲朋友,也有非亞洲朋友。不過在我們學校,大多數亞洲人都會和亞洲人一起玩,但我是個例外,我有白人朋友,也有其他背景的朋友。我在加拿大的青少年時期真的很棒,那是我最美好的時光之一。我覺得那些年讓我成為了一個開朗、快樂的人,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個很開心的人。
Chamath:你的大學生活是那種典型的大學體驗嗎?你是怎麼支付學費的?
CZ:
我每個暑假都會打工,學期中也會做兼職,所以我沒有欠債。我沒有申請學生貸款。第一年,我向我父親借了大約 6000 加元。第二年資金還是有點緊張,我姐姐借給了我 3000 加元。從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向任何人要過錢,完全靠自己養活自己。
Chamath:所以你是從麥吉爾大學計算機科學專業畢業的?
CZ:
其實我沒有從麥吉爾大學畢業。我在那裡讀了四年,但在第三年時找到了一份實習工作,後來一直延長實習期,最後就沒有回到學校。後來我才發現,申請日本的工作簽證需要學士學位,所以我通過一個叫“美國計算機科學學院 (American College of Computer Science)”的在線教育項目拿到了學位。
Chamath:那你當時是在哪家公司實習的?
CZ:
我在東京找到了一份實習工作。其實從大學一年級開始,我就一直在做編程的工作。最初我在一家叫 Original Sim 的公司寫模擬軟件,到了三年級,我加入了一家位於日本東京的公司,叫做 Fusion Systems Japan,他們專門為東京證券交易所的經紀商開發訂單執行系統。
Chamath:當時你是怎麼想的?覺得這是一次冒險,想去東京住一個夏天?
CZ:
是啊,我當時還是大學生,住在東京就像是一個夢想,第一次去那裡就像是來到了未來的世界。當時我主要是寫訂單執行軟件,類似於現在 Binance 所用的軟件。
Chamath:當你第一次接觸這種軟件時,你是立刻覺得“哇,我喜歡這個”嗎?還是說只是因為工作需要,你理解了它的概念,然後去做?
CZ:
一開始只是因為這是我的工作,當時我還很年輕,對各個行業都不太瞭解。其實我剛進公司的時候,他們讓我開發一個數字成像存儲系統,類似於 iPhone 的照片應用,但這是為尼康開發的醫療成像系統。不過很快,我就參與到公司主要的產品——訂單執行系統的開發中。這後來就成了我職業生涯的重點。我喜歡這個領域,因為它需要很高的技術能力,所有的事情都圍繞效率展開,要讓系統儘可能快,處理延遲儘可能低。這種追求效率的過程讓我非常著迷,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對效率非常執著的人。
Chamath:當你看到那些高頻交易公司,他們為了優化效率和降低延遲甚至會設計自己的斷路器,搭建自己的光纖網絡,只為了減少幾毫秒的延遲。這種需求在軟件中是如何體現的?當你編寫這種軟件時,如何在代碼中優化這些邊界條件?
CZ:
首先,你需要確保你的軟件高效快速,比如移除所有的數據庫查詢,把所有數據都存放在內存中。然後儘量減少額外的計算步驟,簡化交易前的風險檢查。更高級的優化是使用 FPGA(現場可編程門陣列),這是一種安裝在網卡上的網絡芯片卡,這樣你就不需要將數據從內存傳輸到處理器再返回內存。
當時我還在寫代碼,大概是十年前,這種往返的延遲大約是 100 微秒。而通過避免這種往返,可以將延遲減少到 20 微秒。接下來,你還可以通過升級物理基礎設施,比如在數據中心進行共置 (co-location),進一步優化速度。
Chamath:在 AI 領域,我們十年前就發現,GPU 的效率很低,比如數據從 GPU 傳到 HBM 再返回的過程非常低效,所以我們直接用 SRAM,在芯片上完成所有操作,這種方法在推理階段的解碼過程中非常高效。那麼,高頻交易為什麼沒有類似的嘗試?我知道 FPGA(現場可編程門陣列)很常見,但為什麼沒有人設計專用的 ASIC(專用集成電路)芯片?還是說其實有人做了,只是我們不知道?
CZ:
我認為這種方式並沒有大規模應用。主要是因為高頻交易的算法變化太快了,硬件設計確實高效,但一旦需要改變設計,會非常耗時。而 FPGA 已經是一個折中的方案了,即便是 FPGA,重新編程的週期也比軟件慢 10 倍。
Chamath:你在日本工作的那家公司成功嗎?
CZ:
很成功,那家公司在 2000 年之前被一家納斯達克上市公司以 5200 萬美元的價格收購。那家公司被收購後,母公司和原公司之間出現了文化衝突。這是我第一次見識到併購並不總是成功的。後來公司的合夥人又創立了一家新公司,但那家公司只維持了一年,因為花費很大但沒有收入。
那家公司倒閉後,我開始尋找新工作。當時 Bloomberg 在招聘,我拿到了工作邀請,後來搬到了紐約。9·11 之後的紐約很安靜,但很快恢復了活力,我在 Bloomberg 工作了四年,做的還是和之前類似的事情。
創辦上海的第一家公司
Chamath:後來你辭職搬到了中國。這是怎麼回事?
CZ:
2005 年初,我在日本認識的一些朋友在討論創辦一家新的金融科技公司。他們都在亞洲,討論過幾個選址,比如東京、上海和香港,他們覺得上海可能是未來金融科技發展的中心。回頭看,我們應該選擇香港,因為從那以後,香港的金融科技發展得更快。所以我在 2005 年搬到了上海,我們一共六個人,想創辦一家新的 IT 初創公司,我們有豐富的華爾街交易技術經驗。我們的想法是,把華爾街的交易技術引入中國,為中國的經紀公司和交易所提供服務。
我們到了上海後,他們又租了一個非常豪華的辦公室,但其他的事情,比如股東權利、優先股和普通股的區別,我一點都不懂。
我完全不知道普通股和優先股的區別。我只是覺得,幹就完了。我算是團隊裡的一個小合夥人。到了中國之後,因為我會說中文,所以我開始和潛在客戶交流。我去找經紀公司談業務,結果發現我們公司註冊的是一家外商獨資企業 (WFOE),而中國的經紀公司和金融機構不能和外商獨資企業合作。
我們是在公司成立後才發現這個問題的,於是公司轉型,開始為任何公司提供 IT 系統服務,類似於外包服務。我們可能會修打印機,也可能會為客戶實施 SAP 系統,我們做了各種各樣的事情。
但我們靠這個活了下來,我們的客戶中有很多是汽車行業的,比如上海通用汽車、上海大眾、上海第一汽車,他們都是我們的客戶。大概三四年後,我們開始在香港開設辦公室,開始與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銀行和瑞士信貸合作。公司逐漸發展了起來,算是成功了。公司現在還在運作。我在 2013 年離開了,待了八年,但公司至今還在。
Chamath:那家公司後來發展到多大規模?
CZ:
最多的時候大概有 200 人,根據我所知,直到現在公司還是維持在這個規模。
Chamath:那作為一個小合夥人,你是靠分紅來賺取收入的嗎?
CZ:
是的,不過其實我們並沒有分到太多的利潤。我當時把大部分存下來的錢又重新投資回了公司,我一分錢都沒有套現。但過了幾年,公司開始變得足夠穩定,能夠支付合夥人不錯的薪水,甚至可以讓我們把孩子送到國際學校接受教育,我們當時的年薪大概是六位數。
Chamath:那時候你已經結婚了嗎?你是怎麼認識你前妻的?
CZ:
我是在第一次去東京的時候認識她的。那是 1999 年,我去東京實習的時候遇到了她,後來她來看我,我們就在紐約結了婚,然後有了孩子,不過現在我們已經分開了。
初識比特幣
Chamath:那麼到了 2013 年、2014 年,後來發生了什麼?
CZ:
我接觸到了比特幣。當時有個朋友對我說:“CZ,你得看看這個叫比特幣的東西。”我說:“什麼是比特幣?”我們聊了一些關於比特幣的事情。
從 2013 年 7 月開始接觸它。當時有一個叫 Bitcoin Talk 的論壇,我從那裡獲取了很多信息。當時 Bobby 對我說:“把你淨資產的 10% 投資到比特幣上吧。最壞的結果是它歸零,你損失 10%。但更有可能的是,它會漲 10 倍,這樣你的淨資產就翻倍了。”我聽完覺得很有道理,於是我開始更認真地學習比特幣,花了六個月時間仔細研究白皮書。
到 2013 年底,我終於完全被說服了,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行動了,但那時候比特幣已經從 2013 年年中的 70 美元漲到了年底的 1000 美元。我當時覺得自己來晚了,我真希望自己能早點入場。其實無論你什麼時候進入比特幣,你都會覺得自己來晚了,因為你接觸的每個人都比你更早買入。
Chamath:那你在學習比特幣的時候,有和別人交流嗎?上海有相關的社區嗎?
CZ:
上海的比特幣社區當時非常小。我基本上是和任何願意和我交流的人交談。我還有幾個在臺灣的朋友,他們當時在臺積電 (TSMC) 工作,嘗試開發比特幣的挖礦芯片。他們後來離開臺積電,想創辦一家初創公司,專注於這個領域。雖然這個公司最後沒有成功,但我當時和他們有過很多交流。
然後最重要的事情發生在 2013 年 12 月。當時在拉斯維加斯有一個比特幣大會,我飛過去參加了。那是一個大約 200 人的小型會議,但整個行業的核心人物都在場,Vitalik、Matt Roszak、Charlie Lee 都在,還有很多其他人。其實很多人到今天還活躍在這個行業。當時會議之前,剛剛發生了 Silk Road 創始人 Ross Ulbricht 被捕的事件。媒體都在報道,說比特幣是毒梟用的工具。但當我去了那個會議之後,我發現與會的都是一群年輕人和極客。他們都非常友好,比如 Vitalik,他是一個非常和善的人。
Chamath:你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還在那家公司工作嗎?是在兼職研究比特幣嗎?
CZ:
是的,然後我回來之後,就和合夥人說,我們應該做一個比特幣支付系統。當時 BitPay 是這個領域的領軍者之一。他們在 2013 年剛剛融資了 400 萬美元,是一個非常大的玩家。
Chamath:所以你當時是想,“我們應該做一個 BitPay 的版本”,然後你的合夥人就說,“你在說什麼?”,而且那時候你自己還沒買過比特幣,對吧?
CZ:
是的,那時候我可能只有一個比特幣。然後我就告訴我的合夥人:“聽著,我覺得這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 那時候我意識到有兩項非常重要的事情:一個是互聯網,但那時候我太年輕了,沒能做太多事情。另一個就是比特幣。當時我 35、36 歲,我不想再錯過了,我覺得下一個類似的技術可能要等 15 年後才會出現。
Chamath:當你去拉斯維加斯,看到那些 22 歲的年輕人時,有沒有覺得自己錯過了機會?
CZ:
其實 35、36 歲還算可以,那時候還不覺得自己特別老。但我當時覺得,下一個類似的技術可能要 10 到 15 年後才會出現,可能是 AI。今天我會說,我生命中有三項基礎性的技術,但那時候,比特幣就是我唯一的關注點。所以對我來說非常清楚,我必須在這個行業做點什麼。
於是我告訴我的合夥人:“我要辭職了,我要投身比特幣行業。” 那時候我們就管它叫比特幣行業。我還需要買比特幣,但我手頭沒什麼錢,所以我決定賣掉我在上海的公寓,用這筆錢去買比特幣。
全力投入加密貨幣行業
Chamath:那你把房子賣了之後住在哪裡?是租了一套公寓嗎?
CZ:
是的。我把房子賣了,當時我的家人也搬到了東京,我們在那裡租了一套公寓住下。 ,而我則繼續在上海和其他地方來回跑。其實那段時間,我也開始和家人逐漸分開了,因為工作關係我需要頻繁出差。
我那套公寓大概以 90 萬美元的價格賣掉了,接近 100 萬美元。然後我就用這筆錢開始買比特幣。因為賣房款是分批到的,每次收到一筆錢,我就立刻用來買比特幣。第一筆錢買的時候,比特幣的價格是 800 美元,然後價格開始下跌到 600 美元、400 美元。我最後的平均買入價大概是 600 美元。
我一邊買比特幣,一邊找工作,我只找比特幣行業的工作,非常明確。但其實我找到工作並沒有花太久,從我決定辭職到最終找到工作,大概也就兩到三週的時間。
Chamath:那麼最後是誰僱了你?
CZ:
我最開始和 BTCC 的 Bobby 談過,他想要僱我。但後來 Blockchain.info 出現了。我遇到了 Roger Ver。當時 Blockchain.info 剛剛成立,創始人是 Ben Reeves,當時剛剛聘請了 Nicholas Cary 擔任 CEO。我是團隊裡的第三個人,職位是工程副總裁 (VP of Engineering),因為我們想保留 CTO 的頭銜給 Ben。
但是後來不太順利,我們把團隊擴展到了 18 人,後來 Peter Smith 加入公司擔任 CFO,他希望為 Blockchain.info 融資。當時 Coinbase 剛剛完成了一輪 3000 萬美元的融資,這在那個時候是行業裡的大新聞。後來公司的文化因此發生了一些變化,我覺得不太適應就離開了,我招募的一些開發人員也相繼離開。我在那家公司待了大概六七個月,最終並沒有取得太好的結果。但這段經歷讓我學到了很多東西。
當我加入 Blockchain.info 的時候,Ben Reeves 告訴我:“我們沒有實體公司,沒有辦公室。所有人都遠程工作,我們只用比特幣支付工資。” 這對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理念,也是我從那家公司學到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而且這種模式直到今天仍然在 Binance 被廣泛應用。我還學到了關於營銷的東西,當時 Blockchain.info 是行業中最大的用戶平臺,而他們的整個營銷策略就是在 Bitcointalk.org 上的一條帖子,Ben Reeves 就是通過不斷回覆這條帖子,把平臺發展成了一個擁有 200 萬用戶的巨頭。
我當時就想,原來可以通過這種遊擊式的營銷方式取得成功。 所以我確實學到了很多東西,但公司的文化變化讓我覺得不適合自己,於是我決定離開。後來何一聘請我加入了 OKCoin。她對我說:“為什麼你要為一家錢包公司工作?你的經驗是處理訂單執行和交易所的。” 所以他讓我擔任 CTO。
當時 OKCoin 向我提供了 5% 的股權,而 BTC China 提供了 10% 的股權,結果 OKCoin 在三小時內就匹配了這個條件。當時 He Yi 在 OKCoin 擁有 1% 的股份,她邀請我成為公司更大的合作伙伴。
就這樣,我加入了 OKCoin,工作了大約八個月。但這段經歷也沒有持續太久,因為我發現 OKCoin 的文化也讓我感到不適。例如,他們的促銷方式讓我不太認同。比如,他們會宣傳手續費折扣,但實際上用戶必須主動申請才能獲得折扣,而不是自動適用於所有人。這些小細節讓我覺得不太對勁。所以到了 2015 年初,我決定離開了。
Chamath:那麼,從那之後你是怎麼開始 Binance 的?
CZ:
2015 年,我和幾個老同事決定在日本東京創建一家比特幣交易所,因為那時候 Mt。 Gox 的崩潰事件已經過去了一年,日本市場出現了一個真空。就在我決定離開 OKCoin 的那一天,有兩個開發人員來找我,然後我們決定成立一家公司,我擔任 CEO,持有更大的股份,並負責融資。我用自己的積蓄支付他們的工資,我自己一分錢都沒拿。
我們三個人很快做出了一個交易所的演示版本,我們下載了一個開源的交易所軟件,然後稍微優化了一下用戶界面,讓它看起來更吸引人。 我當時很坦誠地告訴別人:“我們在兩天內快速做了這個演示。這只是一個概念驗證的原型,用來展示想法,但不是最終的產品。”
我們還寫了一個腳本,從 Bitfinex 獲取市場數據,我們簡單地複製了他們的訂單簿,看起來非常活躍。這個演示非常生動。投資者看到後覺得:“哇,這個技術很棒。” 但這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演示。當他們問我一些技術細節時,我可以給出非常深入的回答。比如他們問我:“你是怎麼設計這個系統,讓它成為一個高效的交易所的?” 我會跟他們講內存撮合、數據庫優化這些技術細節。
以當他們問問題時,我可以深入作答,展現出我的專業知識。他們建議我:“你為什麼不把這套技術賣給其他的交易所呢?因為日本的大多數交易所技術都不太好。” 我覺得有道理,於是我開始和一些交易所接觸。大概兩週後,我們就和其中一家交易所簽了合同,他們花了 36 萬美元買下了我們的系統,並先支付了 18 萬美元的定金,這筆錢足夠支付團隊的工資了,我非常高興。於是我們從計劃運營自己的比特幣交易所,轉型為一家交易所繫統提供商。
大多數人都把創業理想化了,他們以為創業就像 Facebook 的故事一樣,在大學宿舍裡搞個項目,突然就有了上百萬用戶,但實際上像 Binance 或者 Tesla 這樣的公司,成功的過程是一步步艱難摸索出來的,這是一個漫長的努力過程,從一開始並不那麼顯而易見。我覺得 Facebook、微軟和 Google 是少數的例外,它們從第一天起就很成功。但正是這些例外的故事,塑造了人們對創業的錯誤認知。其實,99.9% 的成功企業都不是這樣的,如果你現在去看其他任何成功的公司,幾乎都是通過不斷努力才走到今天的。
幣安的創立之路
Chamath:帶我們回到 Binance 創立的那一刻吧。
CZ:
當時我們正在授權交易所軟件,這個業務發展得還不錯。我們有大約 30 家交易所客戶,這個業務持續了幾年,而且這還是一個 SaaS 模式的業務,我們稱之為“交易所即服務” (Exchange as a Service),我們向客戶收取固定的月費,這些交易所平臺每個月都會支付費用給我們,是個非常穩定的業務。
每新增一個客戶,我們的收入就會有一個臺階的增長。這確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商業模式。但到了 2017 年 3 月,中國政府關閉了我們大部分的客戶,我們當時只是軟件供應商,並沒有直接運營交易所業務,但問題是我們的客戶都沒了,所以我們的業務也沒了。到了 4 月和 5 月,我們就開始討論如何轉型。到 5 月底,我的團隊裡有三個人提議做一個模仿 Poloniex 的項目,Poloniex 是當時最大的交易所之一,但三天後他們又提出要做一個鏈上聊天交易軟件。然後我提議:“為什麼我們不自己做一個交易所呢?我們已經有現成的交易系統,只需要稍微調整一下,改造成一個只支持加密貨幣之間交易的系統。” 於是我們在 5 月決定再次嘗試運營自己的交易所,團隊也同意了。
但是團隊有 20 個人,我們有很多技術人員,但沒有專門的市場團隊。於是我們決定,既然這樣我們就自己來運營一個加密貨幣對加密貨幣的交易所。最開始我們是打算通過風投融資的,但當我看到 Link 的 ICO 成功後,我改變了主意。當時每個人都在談論 ICO,我在 2017 年 6 月中旬參加了一場會議,所有人都在說:“CZ,你必須做一個 ICO,真的得做一個。” 到了 6 月 14 日,我對團隊說:“我們要做一個 ICO,趕緊寫一份白皮書。”
之前在 Blockchain.info 工作的時候,很多人認識我。Blockchain.info 是當時最流行的平臺。而在 OKCoin 時,我是 CTO,也在社交媒體上很活躍。我還負責國際市場的業務,因為團隊裡沒有其他人能用英語溝通得更好,所以在社區裡,我算是有點名氣的。
要做 ICO,你需要有一定的聲望或者資歷,特別是當你在行業早期就參與進來的時候,你去幾次行業會議,可能一開始只有 200 人參加。到第二次的時候大家就會認識你,到了第三次大家就覺得你已經是專家了,所以我在社區裡有一定的聲譽。
Chamath:那麼,誰是 Binance ICO 的買家呢?
CZ:
說實話即使到了今天,我也不完全知道。從人群分佈來看,應該有 80% 到 90% 是中國人,剩下的就是一些國際投資者。數據顯示大概有 20,000 人參與了我們的 ICO,當時 Binance 是一個全新的品牌,只有少部分人因為我的行業背景認識我,僅此而已。
Chamath:所以即使當時中國政府關閉了交易所,但 ICO 是被允許的?
CZ:
那個時候 ICO 並沒有被禁止,確切地說,它既不是被允許的,也不是被明確禁止的。讓我澄清一下:我們之前服務的客戶主要是法幣交易所,而不是加密貨幣交易所。2017 年 3 月時,加密貨幣交易所並沒有被禁止。它們是在我們開始運營 Binance 後的 9 月才被禁止的。
Chamath:你們賣掉了公司多少股份?
CZ:
我們沒有賣掉任何股份,我們只是發行了代幣,沒有股權轉讓。我們推出了一種新的代幣 BNB,這個代幣現在還在流通。我們當時決定出售 60% 的代幣,目標是籌集大約 1500 萬美元,因為我們是用比特幣進行代幣化。
BNB 設計的最初經濟模型,但最主要的是:如果你持有 BNB,當你在 Binance 上進行交易時,可以享受 50% 的手續費折扣,這是我們計劃在平臺上線後很快實現的功能。此外我們還提到,未來 BNB 會擁有自己的區塊鏈和去中心化的生態系統,以及其他三到四個功能。
Chamath:所以當時你們一定很興奮吧?畢竟籌到了 1500 萬美元,現在可以啟動交易所了。但到了 9 月,政府禁止了交易所運營。你們接下來怎麼辦?
CZ:
是的,9 月 4 日中國政府的七個部門聯合發佈了一份通知,宣佈第一,加密貨幣交易所不再被允許;第二,ICO 也被禁止;第三,挖礦也被禁止。我們當時就決定搬走,雖然中國是我們最大的用戶群之一,佔了大約 30% 的用戶,但我們還有 70% 的用戶來自世界其他地方。所以我們覺得,即使失去這 30% 的用戶,我們依然可以生存下去,甚至可以活得很好,於是我說:“我們搬吧,搬到東京去。”
Chamath:當你們剛推出 Binance 的時候,它是一炮而紅的嗎?還是說你們花了很大的努力,才找到產品市場的契合點,吸引了最早的一批狂熱用戶?這種病毒式傳播是怎麼開始的?你們的流動性又是怎麼建立起來的?
CZ:
可以說 Binance 的產品在一開始增長得還不錯,但我們的代幣價格在 ICO 後下跌了。它從 ICO 價格下跌了 30% 到 40%,花了大約三週時間才恢復。當我們推出產品時,由於當時加密貨幣市場依然很火熱,我覺得產品市場契合度是有的。它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想法,只是一個專注於加密貨幣對加密貨幣交易的交易所。
Chamath:
所以 ICO 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對吧?因為用戶會想:“我現在持有這個代幣,我可以享受交易手續費的折扣。” 這就是他們選擇 Binance 的原因吧?但是 Binance 的架構是不是也更好,比如速度更快或者更穩定?
CZ:
是的,絕對是這樣。當時我們上線後,用戶甚至用肉眼就能看出來,在 Binance 上下單的速度比競爭對手的平臺快得多,交易系統的性能是顯而易見的。
當時最大的平臺有 Poloniex 和 Bittrex,中國還有一些交易所,比如火幣和 OKX。在西方市場,有 Coinbase 和 Bitstamp。
Chamath:你是怎麼面對這種成功的?你有沒有想過,“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真的在發生嗎?”
CZ:
確實有一些非常不真實的時刻,但這是那種非常好的感覺。有一次,我問團隊的財務負責人:“我們的收入是多少?” 她說:“幾百個比特幣。” 我當時覺得:“這太瘋狂了,我們不可能賺這麼多……你確定嗎?” 她說:“是的,我們確定。” ,我當時真的覺得這太不可思議了。
還有一段時間特別有意思,就是在上線三週後,BNB 的價格開始恢復。BNB 在 ICO 時的價格是 10 美分,後來跌到了 6 美分。後來 He Yi 加入了 Binance,我們宣佈了她的加入。接下來的兩三週,每次我睡一覺醒來,代幣的價格就漲了 20%。我去開個會回來,代幣又漲了 20%。我去趟洗手間回來,代幣又漲了 20%。
Chamath:那你很快就會意識到,“等等,我已經很有錢了。”
CZ:
這個意識稍微晚了一點,大概是在 2018 年初,也就是六七個月後。《福布斯》把我放在封面上,那時候我才真正意識到。
Chamath:CZ,你覺得什麼是金錢?它重要嗎?我的意思是,不要誤會我的意思,但你是到了 40 多歲才變得富有的。在那個年紀,金錢對你來說還重要嗎?
CZ:
金錢當然還是重要的,但它並不是一切。我覺得我當時已經足夠成熟,能夠以不同的視角來看待它了。首先,我已經 40 多歲了,不再是 20 多歲的年輕人,不會想著買蘭博基尼或者參加奢華派對,我已經過了那個年紀。而且我的性格也比較穩定,不會因為任何事情而過於興奮。此外,不是想炫耀,但我從一個剛剛達到財務自由的人,突然變成了《福布斯》封面上的人物。
我看了看我的錢包,發現什麼都沒有變,即使上了《福布斯》的封面,對我的生活也沒有任何改變。但後來人們告訴我:“你現在可能是億萬富翁了。” 我當時想:“真的嗎?我真的是億萬富翁嗎?感覺並不是這樣。”
就像我們從中國搬到日本的時候,我還訂了一個紅眼航班的經濟艙。然後何一建議說:“也許我們應該升級到商務艙,這樣可以躺下來休息。” 我覺得這確實是個好建議,所以我們就升級了,這種習慣一直延續到後來。
當你逐步賺到更多錢的時候,比如從 100 萬美元到 1000 萬美元,你可能會想買豪車;從 1000 萬到 1 億美元,你可能會想買遊艇;而當你一下子從普通的生活跳到《福布斯》的封面時,你沒有經歷那種逐步的過程,自然也就沒有養成那些消費習慣。
Chamath:那現在呢?現在,根據市場波動,你可能是十億富翁,甚至百億富翁。對你來說,這一切意味著什麼?
CZ:
對我來說意義並不大。我覺得金錢有兩個作用,第一你需要照顧好自己,比如食物和住所,這其實只需要很少的錢。我沒有過奢華的生活,但我覺得我的生活很舒適。 比如我的房子,客廳每隔一個月左右就會漏水,因為房子太舊了,但這個房子對我來說大小剛剛好,能滿足我的需求。很多人以為我住在非常豪華的房子裡,但其實我住的是一個大小適中的房子,能容納我的家人。它不是豪宅,而是一個三手或者四手的舊房子,但位置很好,功能也很實用。
我是一個注重功能的人,只要東西能用,我就滿意了。我不在乎它是否華麗,不在乎它的風格、顏色,也不在乎它是不是鍍金的。只要它能解決問題,我就覺得可以了。
Chamath:CZ,你會感到不安嗎?你有沒有過不自信的時候?
CZ:
其實並不多,我很清楚自己的弱點,也學會了如何去應對它們。所以,我希望自己不是一個特別傲慢的人,我覺得我並不傲慢。我是一個很冷靜的人,其他人的情緒可能會大起大落,比如一會兒開心一會兒又悲傷,而我的情緒波動雖然也有起伏,但幅度很小,相比之下更平穩。
沒有人真正想聽你如何努力工作,他們只想用一種簡單的方式來評價你,比如說:“哇,看看你現在擁有的這些東西。” 但實際上,如果你一直在忙碌,根本沒有時間享受這些,別人是無法理解你所付出的。
Chamath:你覺得自己有一段時間對增長上癮了嗎?
CZ:
我不會說我對增長上癮了,但我確實對工作上癮了,工作本身非常令人滿足,也讓我感到很有成就感。
基本上每天要開 20 多個會議,包括安排好的電話會議、面對面的會議,還有一些臨時的事情。此外我還需要在 Twitter 上回複用戶的消息等等。
不過工作帶來的滿足感很難用語言形容,它並不是來自金錢,也不是因為公司增長,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每日活躍用戶數 (DAU),不是交易量,也不是收入。我認為只要你能夠持續幫助和服務更多的用戶,你就能為他們創造價值。我相信,一個產品的價值體現在人們是否願意使用它。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人想要使用它,即使你的收入是零,這個產品也是有價值的。
這一直是我的理念。當然,你可以優化短期的收入和利潤,但那可能會犧牲長期的增長。我相信,從長遠來看如果有大量的人使用你的平臺,你就能為自己和用戶創造價值。人們之所以選擇使用你的平臺,是因為他們覺得使用你的平臺能帶來價值,所以這就是我的核心目標。
此外,與此相關的是,知道有數以億計的人在使用我們的平臺,我覺得我們是在幫助他們。我的看法是,如果用戶願意支付手續費,那是因為我們一定為他們提供了更高的價值。
Chamath:每日活躍用戶數 (DAU) 雖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指標,但它也有雙刃劍的一面,因為其中可能會有一些惡意行為者。你第一次意識到這可能是個問題,並且需要認真對待是什麼時候?是不是有人跟你說:“CZ,我有好消息和壞消息。” 那次會議是什麼樣的?
CZ:
是的,我記得非常清楚。大概是 2018 年的元旦,那時候我們剛剛成立五六個月,但 Binance 已經是全球最大的交易所了。 在 2017 年的除夕夜,也就是 12 月 31 日左右,美國國土安全部的一位官員聯繫了我。他給我發了一封郵件,說希望我們協助追蹤一些黑客的資金流動,這些資金可能是從 2017 年 EtherDelta 被黑事件中盜取的,EtherDelta 是當時一個去中心化交易所,後來因為黑客攻擊而關閉了。
這位美國政府的官員發郵件給我們時,我完全不知道該怎麼處理。我們的團隊裡也沒有人有和執法機構打交道的經驗。所以,我召集了幾個人開了個小會,討論該怎麼幫助這位官員。首先,我們核實了他的身份,確認他確實是執法機構的人。然後,我們提供了他所需要的信息。他後來對我們表示了感謝。
我還問他:“你能不能推薦一個可以幫助我們與執法機構打交道的專業人士?” 他確實推薦了一個人,但那個人在美國,而我們當時沒有美國實體,所以無法僱用他,最終這件事就擱置了。但那一天對我來說是一個轉折點,我意識到我們需要一個有與執法機構合作經驗的專業人士加入團隊。 我們最終僱傭了更多有相關經驗的人。
我可能在法律上有一些限制,不能詳細討論認罪協議等內容。我不是律師,所以我會盡量避開這些話題。不過,總體來說,我只能說拜登政府對加密貨幣是相當敵視的,他們甚至公開宣佈對加密貨幣開戰。
所以現在看到新一屆政府的態度發生了 180 度的轉變,我覺得這對美國和全世界來說都是一件好事。當然我不會去責怪上一屆政府,但我覺得他們可能對加密貨幣的瞭解不夠。
Chamath:你覺得他們為什麼對加密貨幣如此敵視?
CZ:
我覺得這主要是對新事物的恐懼。我想他們可能在腦海中有一種想法,就是不要破壞現有的金融系統,而且這些行業可能也對他們進行了大量的遊說,這或多或少影響了他們的思維方式,甚至可能讓他們產生了一些偏見,這是人類的天性。
FTX 故事:與 SBF 的關係及其崩盤始末
Chamath:後來你開始看到一些其他人也開始嶄露頭角,比如 SBF 和 FTX 開始快速崛起。和我聊聊吧,你是怎麼認識他的?因為你後來還持有了他們不少的股權。
CZ:
是的,我們確實投資了 FTX,但只持有 20% 的股權,而且我們只持有了一年就退出了。我第一次見到 SBF 是在 2019 年 1 月,在 Binance 在新加坡舉辦的一次會議上,我記得當時 FTX 還沒有成立,SBF 還在經營 Alameda。他們在新加坡聖淘沙的水族館裡舉辦了一場派對,甚至安排了潛水員在魚缸裡舉著寫有“Alameda”等字樣的標誌。他們是 Binance 的 VIP 客戶,也是一個大交易商,所以我們對他們的態度很友好。
那是我第一次見到他。幾個月後他們來找我們,說想啟動一個期貨交易平臺。他們提議合作建立一個期貨平臺,類似於一個合資企業。他們提議按 60-40 的比例分成,對我們有利。當時我想過反駁,因為我們有所有的用戶,而他們當時什麼都沒有。所以我們拒絕了。
Chamath:他們當時是你們流動性池中的重要部分嗎?
CZ:
也不是特別重要。他們是一個大交易商,但 Binance 本身也剛剛起步。他們在我們平臺上活躍的時間也不長,大概只有六個月到一年。
後來,在夏天的時候,他們帶著更好的提議又來了,但我們還是拒絕了。到了 11 月,他們又提出了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提議。那時 FTX 已經上線,並且積累了一些交易量。他們提出以一個非常優惠的價格給我們 20% 的股權,同時進行代幣互換,用 BNB 換 FTT,我們得到了初始的一些 FTT 代幣。當時 BNB 的流動性更高,而 FTT 的流動性較低,我們最終達成了這筆交易。
但幾乎在交易完成後不久,我就開始聽到一些朋友說 SBF 在美國的華盛頓圈子裡對我們說壞話。我覺得很無奈。此外,他們還做了一些讓人不快的事情,比如用五倍的薪水挖走我們負責 VIP 客戶的客戶經理,這些人掌握著我們的 VIP 數據庫。然後,這些員工剛到他們公司,我們的 VIP 客戶第二天就接到電話,說在 FTX 可以拿到更好的費率。我給 SBF 打電話說:“能不能別再這樣了?我們可是你們的股東啊。” 他一邊答應著,一邊又邀請我一起參加加密貨幣活動做一對一的訪談。我同意了,因為作為投資者,我也希望幫助推廣 FTX。我其實希望行業裡有多家成功的交易所,這樣我們 Binance 就不會總是成為被針對的目標,但即便如此我還是不斷聽到他們在背後說我們的壞話,或者做一些其他不太友好的事情。
大概一年後,也就是 2021 年初,他們聲稱正在以 320 億美元的估值籌集資金,根據我們的投資條款,我們對他們的後續融資有否決權。如果想阻止他們,我們是可以這麼做的。但我並不想用這個權利來阻礙他們的發展。所以我們決定退出,和他們公平競爭。我們最終達成了協議,如果我沒記錯的話,交易是在 2021 年 7 月完成的,轉讓也在那時候完成。
Chamath:那是在他們爆發問題之前整整一年半的時間,有傳言說,他們的問題是在你們出售股份後才開始的,而且和你們的退出有關。
CZ:
是的,那完全不是真的。而且,由於業務的競爭性,即使我們是股東,我從來沒有向 FTX 索要過財務報表。我是一個非常被動的投資者。當我投資時,我不會參與他們的業務。而且我們之間本身也有一些競爭關係,比如我們有期貨平臺,他們也有期貨平臺。所以我儘量保持距離,讓他們自己去做自己的事情。
Chamath:關於 FTX 的崩盤,人們討論最多的有兩點。第一是賠償方式對一些 FTX 用戶來說並不理想,尤其是那些存款在平臺上的用戶。第二是關於一些投資的價值在事後變得一文不值。你怎麼看待這一切?這些事情對整個行業有什麼啟示嗎?
CZ:
我在網上看到過很多不同的說法,為了透明起見,我要說明,目前我們和 FTX 的遺產管理方之間還有一場正在進行的訴訟。他們試圖追回我們在一年半前退出時獲得的一些資金,所以我可能不能說太多。不過,我確實聽到了一些抱怨,比如有些中國用戶不符合賠償資格等等。但根據我讀到的內容,由於加密貨幣價格的上漲,現在以美元計算,資金總量是足夠的。雖然如果用戶當時持有的是加密貨幣,可能現在會得到更多。
面對拜登政府的反加密貨幣政策與司法部調查
Chamath:你是什麼時候開始覺得 Binance 的事情變得複雜的?
CZ:
對我來說,複雜的事情開始於他們向我們索要信息的時候,他們提出了一些信息請求,而我們一直都很配合。這大概是在 2021 年到 2022 年期間。到了 2022 年底,他們的態度變得更為敵對。然後在 2023 年初,他們的立場變得更加明確——要麼我們達成某種協議,要麼他們會起訴我們。事情就變成了談判。
Chamath:那你是怎麼應對的?會不會覺得“我簡直不敢相信這是真的”?比如,當你參加會議時,律師或者其他人告訴你:“CZ,我覺得可能會有起訴。” 那種會議是怎麼樣的?
CZ:
首先,我沒有法律背景,所以我必須依賴別人的建議。這對我來說是最困難的部分,因為我在這方面完全沒有經驗。其實,沒有人會有這樣的經驗。經歷過一次的人也不想再經歷第二次,對吧?所以,作為被調查的一方,基本上沒有人有經驗。
我們僱了一群律師,他們都很優秀,但協調他們其實非常複雜。請來的律師可能來自不同領域,有不同的專業方向,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見。而且,他們都想表現得自己是最聰明、最重要的那一個。他們花費的時間越多,收費也就越高。我並不是說他們不專業或不道德,他們確實想把事情做到最好。但問題是,他們會提出各種不同的方向,導致我們被拖入各種複雜的討論中。
對我來說,這才是最麻煩的部分。如果有人能直接告訴我需要關注什麼那會簡單得多,但我們的法律團隊還很年輕,缺乏處理這種複雜問題的經驗,所以事情變得更加棘手。
我們團隊在那個時候已經分散在世界各地了,我自己在 2023 年的時候主要在迪拜和阿布扎比之間來回奔波,所以那段時間真的非常有壓力,但我應對壓力的方法是分析最好的和最壞的情況。我會問團隊:“最好的情況是什麼?” 比如說,“好吧,我們支付一筆罰款,達成延緩起訴協議 (DPA),然後事情就結束了。” 這是最好的情況,最壞的情況是他們可能會把我送進監獄。”
Chamath:但那真的是最壞的情況嗎?因為當時看起來,最糟糕的情況可能是某種形式的緩刑。
CZ:
確實如此。在我之前,沒有人真的因為類似的事情被送進監獄,但他們可以提出這樣的要求。還有一種更糟的情況是,如果我們無法達成協議,就只能選擇抗爭。這樣的話我可能會留在阿聯酋,因為它是一個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現在我已經是阿聯酋的公民了,幾乎不可能被引渡,但這樣的話我的旅行會受到很大限制。即使去一個沒有引渡條約的國家,也可能面臨一些風險,因為這些國家之間可能會達成某種協議,這種生活會充滿不確定性和恐懼。
這會製造很多麻煩,也可能給阿聯酋政府帶來很大的壓力,我不想給那些給予我公民身份的人帶來麻煩,我不想成為一個麻煩製造者。但最糟糕的情況就是,他們起訴你,把你列入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名單,這種情況也是有可能發生的。
Chamath:那你最後是怎麼解決的?
CZ:
談判過程非常漫長,基本上每天都要和 12 到 20 名律師進行電話會議,這種情況持續了一年多。我們和拜登政府的司法部 (DOJ) 之間來回拉鋸了一年多,我從律師那裡聽到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們從來沒有見過他們對一個案件如此敵對。” 這幾乎成了我聽到的口頭禪。
Chamath:在這個過程中,你會不會逐漸對這些事情感到麻木了?還是說你會一直把這些事情放在心上,覺得“為什麼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你會不會感到怨恨,還是說你是以其他方式來應對的?
CZ:
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有幾個階段特別難熬。在談判中,有一些關鍵時刻,我們只能說不,比如說,他們提出了一些條件,我們無法接受,而他們又不願意讓步。
然後會有幾周的時間過去,你根本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這是一種煉獄般的狀態。你隨時可能被起訴,完全取決於他們的決定。而你已經拒絕了他們的條件。在這幾周裡,我會不斷地心理建設,比如:“我可能哪都不能去了。我可能必須習慣只待在一個國家,過上非常小心的生活。也許在某個邊境口岸,會有一個未公開的起訴令等著我。”
有趣的是,過了兩週後,他們又回來找我們,說我們可以繼續談判了。現在回頭看,我覺得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談判策略。對於我或者任何處於我這種情況的人來說,這種沉默和拖延是一種心理戰術。
對於被調查的人來說,這種事情一生可能只會經歷一次,所以沒有經驗,但對他們來說,這就是日常工作。這關係到你的生活,因為可能有一個密封的紅色通緝令等著你,而這種狀態可能會持續幾十年。
他們非常有經驗,知道如何通過心理戰來施壓。我認為他們很清楚,兩週是一個最佳的時間。如果時間更長,你可能真的會習慣這種狀態。所以他們不會讓你在這種狀態下待太久。他們在這方面真的很有經驗。
Chamath:那你是怎麼讓自己最終同意達成協議的?
CZ:
經過多輪談判後,我們基本上達成了一項協議,承認我違反了《銀行保密法》(Banking Secrecy Act) 中的一項規定,也就是未能按要求完成註冊。這是一項聯邦犯罪,確實性質很嚴重,但歷史上從未有人因為違反這項規定而被判入獄。
Chamath:抱歉,這個指控聽起來更像是一個技術性問題。那它和美國媒體中所描述的,比如洗錢、協助犯罪、沒有進行 KYC 和反洗錢 (AML) 措施等,究竟有什麼關係?媒體的認知和實際指控之間是完全一致的嗎,還是有很大的出入?
CZ:
當然,我可以試著解釋一下我的理解。不過首先我需要聲明,我並不是律師,所以以下只是我的個人觀點,可能會存在偏差。
首先,最基礎的指控是違反了《銀行保密法》(Banking Secrecy Act),具體來說就是沒有按照規定完成註冊。簡單來說,我們在為美國用戶提供服務時,並未在美國註冊為金融服務公司。這確實是我們的疏忽,但這個問題與用戶是否從事了任何不法行為無關。問題的核心在於,我們沒有向美國相關機構註冊,以表明我們有資格為美國客戶提供服務。
在此基礎上,他們還提出了關於我們 KYC(瞭解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和 AML(反洗錢,Anti-Money Laundering)程序的指控。他們認為我們的 KYC 和 AML 程序不夠完善。很多人可能以為 KYC 和 AML 是非黑即白的事情,但實際上並非如此。這涉及到你在實施這些程序時的深度,比如所使用的系統、操作流程、人員配置等許多細節。
更嚴重的指控是,他們可能會質疑我們是否“明知並協助了不法交易”。舉例來說,可能因為我們的 AML 程序不夠完善,未能識別出某些不法行為者的交易,但這與“明知道這些交易是非法的卻仍然促成它們”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更高一級的指控則是個人直接參與了這些非法交易,比如早期加密貨幣行業中,Charlie Shrem 協助 Silk Road 的 Ross 處理非法交易的案例。而我個人從未直接參與過任何交易,這既不是我的工作職責,我也絕不會去做。
最終,他們對 Binance 的指控主要集中在兩點:第一,未完成註冊;第二,KYC 和 AML 程序存在不足。通常來說,這些問題是可以通過繳納罰款來解決的。根據歷史記錄,在沒有其他附加罪名的情況下,美國從未有人因為這些單一的指控而被判入獄。
然而,政府還試圖對我增加兩項額外的指控,他們稱之為“增強指控 (enhancements)”,也就是第三和第四項。這些指控聲稱我個人協助了某些不法行為,但他們並沒有任何確鑿的證據來支持這些指控。他們試圖通過公司的一些行為間接地將責任轉移到我個人身上。
Chamath:他們能具體指出某些交易或者其他的事情嗎?
CZ:
沒有,他們並未提供任何具體的證據,因此這兩項“增強指控”最終被法庭直接駁回了。在我前往美國之前,我們已經達成了一致意見,將在法庭上對這些指控進行辯護。而且根據我當時的理解,從未有人因為類似的指控而被判入獄。
在歷史上,因類似問題受到最嚴厲懲罰的人是 BitMEX 的聯合創始人 Arthur Hayes。他因 BitMEX 的合規問題被判處了六個月的居家監禁,當我研究他的案件時,我發現他與客戶有更多直接的互動,而在 Binance,我的角色幾乎沒有涉及直接與客戶的接觸。我主要是在 Twitter 上與用戶互動,但並不參與 Binance 的後臺操作流程。因此,我認為我們的情況相對有利,基於這些原因,我相信我們選擇的解決方案是最好的。
Chamath:所以你同意了這些指控,並表示會在法庭上就第三和第四層指控進行辯論。然後你來到美國,進入法庭,開始這個過程。接下來發生了什麼?
CZ:
是的,這個過程充滿了複雜的細節。首先,第一天我前往法庭認罪。在這之前,認罪協議已經經過了許多律師的反覆討論和修改。第二天一早,我再次前往法庭,正式開始程序。
法庭程序的第一步是認罪。法官會逐條詢問每一段協議內容,比如:“你是否理解這段內容?這一段呢?還有這一段?” 我只需要逐一回答“是,是,是”。由於這些內容此前已經被律師們反覆審核過,可以說整個協議已經被“過度法律化”了。接下來,爭論的焦點並不是指控本身,而是我的保釋條件。
我的律師認為,我應該被允許返回阿聯酋,等待三個月後的判決。但政府擔心我可能不會如期返回,因此希望我留在美國。不過,他們也承認,我對社會沒有任何威脅,因此不會限制我在美國的行動。雙方圍繞這個問題展開了激烈的爭論。
最終,第一位負責此案的治安法官裁定我可以離開美國,回到阿聯酋等待判決。這對我來說本是一個理想的結果。然而,政府對這一決定提出了上訴。我的律師告訴我,他在 40 年的職業生涯中從未見過有人對保釋條件提出上訴。他還補充道:“這樣的行為只會惹惱法庭,可能對你反而有利。”
然而,兩週後,法院裁定政府勝訴,我被要求留在美國,無法返回阿聯酋。
因此,我不得不離開家人,在美國滯留三個月。雖然我在美國境內可以自由活動,但我仍然覺得自己被困在這裡,無法回家。幸運的是,我的姐姐在美國有一處房子,我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之後,為了調整心態,我開始四處旅行,讓自己冷靜下來。
三個月後,政府再次要求延長我的滯留時間,又增加了三個月的等待期。
Chamath:那時候你的孩子們有來看過你嗎?
CZ:
沒有,我沒有讓他們來看我。實際上,那一年我都沒有見到他們。隨後,政府又提出了再延長三個月的請求。最終,我的法庭日期被定在了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那之前的一週,雙方需要提交最終的請求文件。
讓我震驚的是,政府在請求文件中要求判我 36 個月的刑期,這已經是量刑指南上限的兩倍。法庭甚至表示,他們從未見過政府要求法庭無視量刑指南的案例,這種情況讓我感到非常意外。
我是在開庭前一週得知政府的請求內容的,因為他們需要提前提交書面請求。當我聽到這個消息時,心情非常沉重。更讓我感到不安的是,我的律師的態度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之前他們還告訴我,我可能會被允許回家,但後來卻改口說,法官可能會在政府的請求和我們的請求之間選擇一個折中方案。政府要求判我 36 個月,而我們則請求判緩刑。
更讓我感到意外的是,就在我被判刑的前五天,也就是 4 月 25 日,參議員 Elizabeth Warren 在電視上公開表態,宣佈對加密貨幣“宣戰”。而我的判決日就在五天後。她還向司法部遞交了一封公開信,其中提到了一些與我相關的內容,但大部分信息其實並不準確。這無疑讓我感到更加緊張。
終於到了 4 月 30 日,我的判決日。法官在法庭上說了很多關於我的好話,這些話我後來都收錄在了我的書裡。然而,就在我稍稍鬆了一口氣時,法官突然說道:“但是……”,聽到這個詞,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我知道這可能不是一個好兆頭。
在判決當天,律師們仍然在法庭上爭論刑罰的內容。幸運的是,法院駁回了政府提出的兩項“增強指控”。我的律師辯稱,我從未直接處理過任何交易,也對相關的事情並不知情。因此,法庭直接否定了第三和第四層指控。
最終,法官作出了判決:四個月的刑期。
聯邦監獄的生活
Chamath:你是怎麼應對的?
CZ:
一開始真的很難熬,這不僅僅是四個月的刑期問題,更重要的是“我會不會安全”的問題。你想想,如果有人能明確告訴我:“你只需要在這個地方待四個月,而且絕對可以保證你的安全。” 那我會覺得沒什麼問題,可以接受,但讓我感到最不安的,是未知和不確定性。
尤其是在判決之後,一些主流媒體開始高調報道,說我可能是歷史上進入美國監獄的最富有的人。我的律師和監獄顧問對此非常擔憂,他們告訴我,由於這些報道,我在監獄裡很可能會成為勒索的主要目標。他們明確表示,我的安全可能會面臨很大的威脅。我不停地問自己:“我該怎麼辦?進去之後什麼都沒有,我該怎麼保護自己?”
為了應對這些擔憂,我聯繫了很多人,包括一些專業的監獄顧問。這個職業其實是一個非常特殊的行業,顧問通常是一些前獄警、前典獄長,或者曾經服過刑的前囚犯。他們的工作是幫助像我這樣的新人提前瞭解監獄的生活,提供一些實用的建議,比如如何與人相處,如何保護自己,甚至如何避免衝突。
這些顧問告訴我,由於我的案件備受關注,我很可能會成為被勒索的目標。他們給了我很多建議,比如在監獄裡儘量不要交朋友,尤其是第一天如果有人對你特別友好,不要接受他們的任何東西,因為他們可能以後會要求你十倍地償還。而如果你拒絕或無法償還,他們可能會對你採取暴力手段,比如直接對你動手甚至傷害你。
這些建議確實讓我有所準備,但最終無論有多難,你只能硬著頭皮去面對。我在美國監獄裡學到了一些事情。首先,美國的監獄系統非常龐大,大約有 200 萬人被關押在監獄中。美國政府每年在監獄上的花費甚至比在教育上的花費還要多。這說明美國的監獄人口有多麼巨大。
此外,美國有 50 個州,每個州都有自己的監獄系統,還有州立監獄和聯邦監獄。每個監獄就像一個小城市,我所在的監獄有 2200 名囚犯,真的像一個小城市一樣,每個監獄都有自己的規則。雖然我在進去之前得到了很多建議,但很多建議其實並不適用。
Chamath:你是在 4 月 30 日被判刑的,那你什麼時候開始服刑?
CZ:
當你被判刑時,你並不會立即知道自己會被送到哪所監獄。法庭會推薦兩所監獄作為選項,然後你會收到一封信,通知你具體的報道日期。在我的情況下,法官裁定我不需要接受任何監管,這其實是非常少見的情況,所以我不需要被戴上手銬帶走,也不需要被關押。我只需要等待一封信寄到我姐姐的住址,這是我在法庭上登記的地址。
實際上司法部曾要求立即將我戴上手銬帶走。我懷疑他們是想拍一張我被捕的照片,用作宣傳。但法官拒絕了這一要求,他表示:“他不是危險分子,也沒有逃跑風險,我不會這麼做。” 法官甚至特別補充了一句,說我不需要任何形式的監管。後來我瞭解到,這種裁定其實是一個非常罕見的法律條款。這也是為什麼在我服刑結束後,我沒有緩刑或假釋的要求,也不需要接受任何後續監管。
Chamath:這段時間對你來說怎麼樣?有沒有發生什麼糟糕的事情?
CZ:
幸運的是,入獄期間沒有發生什麼特別糟糕的事情,但是這段經歷本身就已經很糟糕了,我至少沒有受到身體上的傷害,也沒有參與打架,更沒有真的被勒索。
在進入監獄之前,我的監獄顧問給了我很多建議,比如儘量不要加入任何幫派,保持獨立,低調行事。然而,就在我剛走進監獄大門時,一名獄警對我說:“你可能需要一些保護。我聽說太平洋島民在招人,你可能想加入他們。” 這是我剛進門時聽到的第一句話,讓我非常緊張。
監獄的第一天非常忙碌。他們會帶你經歷一系列的流程,比如脫衣搜身。我在 CNBC 上也提到過這件事,他們會對你進行非常徹底的搜查,然後將你分配到一個單元。我被分配到的單元裡有大約 200 名犯人,牢房分為三排,每排 20 個牢房,兩兩相對,共三層樓。底層是一個公共區域,供犯人活動。
當你第一次走進牢房時,幾乎所有囚犯都會盯著你看,其中很多人都是肌肉發達的壯漢,這種場景讓我感到非常緊張。監獄會按照種族來組織囚犯,也就是根據你的族裔分組。如果你是中國人,他們會把你分到中國人的組裡;如果你是白人,你會和白人一組;黑人和黑人一組;墨西哥人和西班牙裔會被分到一組。這種分組在一定程度上確實減少了衝突。因為從文化和習慣上來說,你更容易和同種族的人相處。監獄的管理人員甚至鼓勵這種種族分組,因為這可以有效地降低衝突和打架的概率。
一旦你被分到一個組,如果你和其他組的人有問題,會有一個代表出面調解。每個組都有一個代表,類似於工會代表,他們會聚在一起討論問題,所以監獄裡其實有一套自己的規則和體系,但我當時對這些一無所知。
剛進去的時候,一個看起來像亞裔混血的傢伙走過來對我說歡迎加入我們的組。我當時心想:“我該和他握手嗎?還是不要?我是不是加入了某個幫派?” 後來我瞭解到,這個傢伙是菲律賓和德國的混血兒。因為監獄裡的亞洲人很少,所以他們把所有看起來像亞洲人的人分到同一個組裡。這其中還包括原住民和太平洋島民,比如夏威夷人。在我們這個 200 人的監獄裡,我們這一組總共只有 6 個人。
其實,我本應該被送到最低安全級別的監獄(Minimum-Security Prison),那裡的囚犯主要是犯了經濟類罪行的人。但因為我不是美國公民,他們把我送到了低度安全的監獄(Low-Security Prison),這裡的囚犯大多是因為毒品犯罪而入獄的,這真是一段特別的經歷。
Chamath:你出獄後做的第一件事是什麼?
CZ: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好好洗了個澡,然後吃了一頓美味的飯。在監獄裡,淋浴間非常小,幾乎就像一個封閉的盒子,淋浴間的門設計得像西部牛仔酒吧那種門,只能遮住中間的部分,頭和腿都是露在外面的,而且空間非常狹窄。
所以,當我第一次出獄後,能夠在一個寬敞的淋浴間裡洗澡,不用碰到牆壁時,我感到這簡直是一種奢侈的享受。
還有食物的問題。在監獄裡,水果非常稀缺,優質蛋白幾乎沒有。當我出獄後,看到一盤擺滿水果的餐桌時,我心裡想:“天啊,這簡直是幾個月沒見過的奢侈品。”
Chamath:那你是立刻回到了阿聯酋嗎?
CZ:
是的,離開監獄後,從走出監獄大門到登上飛機飛離美國,大概只花了 26 分鐘。
Chamath:
那時候你在想什麼?你有沒有覺得:“我能理解他們的立場,至少在某些指控上我覺得有道理。” 還是你覺得這完全是一場不公正的迫害?
CZ:
關於認罪協議和相關內容,我有一些法律上的限制,不能透露太多,但是從情感上來說,我當時只想讓這一切快點結束。
你要知道,我剛出獄的時候還是拜登政府執政,選舉還沒有發生。誰會贏得選舉還不確定,美國的政策是否會改變也不確定。我當時的想法是,如果政策繼續下去,美國可能還是會採取反加密貨幣的政策。無論如何我們只能盡力去適應並生存下去。
Chamath:那麼當你回到阿聯酋後,你是否接受了不能再管理 Binance 的事實?因為這是認罪協議的一部分,對吧?
CZ:
我接受了這個事實,辭去 Binance 的管理職位對我來說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我當時甚至哭了。這次辭職讓我感到非常複雜,一方面,我對 Binance 有著深厚的感情,畢竟這是我一手創立並傾注了大量心血的公司;但另一方面,我也知道這是我不得不做出的選擇。
如果是我自己主動辭職,可能會有人說:“這個人撐不住了。” 但現在是因為我被法律限制,不能再管理 Binance,這不是我的選擇,也不是我的問題。所以後來我想通了,我的人生中還有很多其他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去做。
Chamath:申請赦免的過程是怎樣的?你為此做了什麼?赦免的意義是什麼?
CZ:
關於赦免,其實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流程,甚至可以說很少有人真正瞭解它的具體操作方式。我瞭解到的情況是,你需要找一位律師,幫助你起草一份請願書。在這份請願書中,你需要詳細說明為什麼你應該被赦免,例如你是否受到了過度的起訴,或者你是否證明了自己是一個值得信任的好人。
赦免的意義在於,它可以完全抹去你之前的法律記錄,讓你重新迴歸普通人的身份。至於被赦免的理由,其實可以是任何事情,這完全取決於總統如何看待你的請願書。
根據我的理解,美國憲法賦予總統赦免權,但並沒有詳細規定具體的操作流程。總統在行使這個權力時,往往會受到社會氛圍和個人判斷的影響。比如從歷史上看,大多數總統都會選擇在任期的最後一天進行赦免,這似乎已經成為一種傳統。不過,拜登總統在這方面採取了一些不同尋常的做法。他不僅在任期中間赦免了一些人,還首次引入了“預赦免”的概念。所謂“預赦免”,是指在相關司法程序完成之前就提前赦免某人。這種做法在美國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他甚至對自己的兒子進行了某種形式的預赦免,這也引發了不少爭議。
總的來說,我瞭解到的赦免流程是這樣的:總統可以根據自己的意願決定是否赦免。你需要提交一份請願書,然後耐心等待結果,這個過程通常沒有明確的時間表,結果可能會在某一天突然發生。
Chamath:有些人可能會猜測,你為了獲得赦免做了什麼。你想對這些猜測做出回應嗎?
CZ:
其實我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情,不過,我覺得如果沒有赦免,Binance 很難以正規的方式進入美國市場。因為我是 Binance 和 Binance US 的最終受益所有人。如果沒有赦免,Binance 在美國的業務會受到很大限制。
從更大的角度來看,如果美國想成為全球加密貨幣的中心,就不可能忽視像 Binance 這樣的重要市場參與者。畢竟,美國也不能讓自己的公民失去接觸全球最大加密貨幣流動性池的機會。此外,Binance 還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貨幣生態系統之一,在行業中佔據著重要地位。因此,我猜測可能是總統對加密貨幣持支持態度,這才促成了這次赦免。
總統自己也經歷過類似的事情,比如被銀行拒絕服務 (debanking),甚至面臨 34 項刑事指控。我還記得在監獄裡通過電視看到他被起訴的新聞,其中一項指控是他把一些文件帶到浴室閱讀。
我想,正是因為他自己經歷過這樣的事情,所以可能對我的處境產生了一些同情。他或許也很清楚,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在處理這些案件時有多麼激進。這種同情心,也許在某種程度上幫助了我獲得赦免。
離開幣安後的新生活與創業冒險
Chamath:現在你是怎麼安排時間的?
CZ:
其實我現在還是挺忙的,我在運營 Giggle Academy,這是一個免費的教育平臺,我也為很多政府提供諮詢,幫助他們制定合理的加密貨幣監管政策。同時,我也參與投資,主要是區塊鏈、AI 和生物科技領域。
這些是 Binance 之外的項目,是 YZi Labs 的一部分。此外,我還會指導和輔導一些 BNB Chain 生態系統中的創業者。這些事情加在一起,讓我一直很忙。
Chamath:能和我說說 Giggle Academy 嗎?
CZ:
我一直認為,我們完全可以把所有的教育內容數字化,而這件事非常重要,因為有一些令人震驚的數據:全球有 7 到 8 億成年人是文盲,其中三分之二是女性。另外,還有大約 5 億孩子沒有上學。加起來大概有 12 億人沒有接受教育,佔全球人口的 12% 到 13%。
這些人主要生活在非常貧困的地區,那裡的學校資源極其匱乏,或者家庭根本負擔不起學費,而且即使有學校,教育質量也不高。學校的教學模式往往會把學生的表現“平均化”,無法因材施教。
Giggle Academy 是一個手機或平板上的應用程序。我相信,通過遊戲化設計、人類心理學的研究以及 AI 技術,我們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應用程序提供所有的教育內容,而且完全免費。我的目標是解決教育的可及性問題,讓更多人能夠接觸到教育資源,當然我也希望未來能夠提高教育質量。
Chamath:你對 Giggle 的設想中會有學校的存在嗎?
CZ:
我並不想做學校。我希望每個人都能通過一個應用程序學習。這個軟件非常注重獎勵機制,比如通過徽章來激勵學習。
Chamath:當我聽到這個項目時,我的第一反應是,這些徽章是否可以和代幣化、獎勵機制以及支付系統掛鉤?這是我的聯想,還是確實有這樣的計劃?
CZ:
我對此思考了很久,但我決定不會在 Giggle Academy 上發行代幣。如果發行代幣,我們可以實現“學以致賺 (Learn-to-Earn)”的模式,用代幣激勵學生學習和老師製作內容,這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機制。
但我不想發行代幣的原因是我自己。如果 Giggle 發行了代幣,所有人都會想買這個代幣,平臺上的人可能不再是真正的孩子,而是一些“礦工”在挖代幣。我希望 Giggle 是一個真正免費的教育平臺,而不是一個以代幣為中心的加密項目。如果引入代幣,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會被代幣吸引,而不是教育本身。
Chamath:所以你的目標是通過自籌資金來支持這個項目,並持續推動它的發展?
CZ:
是的,不過後來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有一個社區項目捐贈了大約 1200 萬美元,而我到目前為止只在這個項目上花了 300 到 400 萬美元,所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在這個項目實際上已經實現了資金盈餘。
其實,把錢用在有積極影響的地方是很難的,想要讓資金真正產生正面的社會影響,這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難的事情。所以我的計劃是,只要有需要我會一直資助這個項目,直到實現目標:通過一個遊戲化、吸引人的方式,完全數字化地提供教育。
Chamath:你提到 AI 是你生活中的第三個重要支柱,你也看到了它帶來的巨大浪潮,對吧?
AI 最有趣的地方之一是,當你深入研究嵌入 (embeddings) 和嵌入層時,你會發現它其實是一種機器可讀的語言,而不是英語。這種語言包含了豐富的信息,非常適合 AI 智能體 (AI Agents)。智能體可以在這種語言中操作、解碼、查詢,從而實現生產力的巨大飛躍,智能體也可以成為商業活動的參與者,它們需要支付系統。
我記得你曾說過,在不久的將來,加密貨幣可能會成為智能體最大的用戶。能否為我們描述一下你的這個願景?
CZ:
是的,我覺得這個願景其實非常清晰。正如你所說,我相信很快每個人都會在後臺擁有成百上千甚至上百萬的智能體為我們工作,而這些智能體會不斷進行交易和資金轉移。
智能體的交易頻率和交易量將遠遠超過人類,它們不會使用傳統的銀行系統,因為銀行無法處理智能體的開戶、反洗錢 (AML) 或客戶身份識別 (KYC),這些流程對於智能體來說完全沒有意義。
此外,智能體的交易速度和規模會遠超傳統的支付網絡,傳統銀行系統可能根本無法支持這樣的交易需求。
智能體在投資和交易領域也會帶來革命性的變化。比如,現在如果你想在 Binance 上交易,你需要打開應用程序,查看圖表,手動輸入價格,然後點擊買入或賣出按鈕。但未來,你只需要告訴智能體:“把我 10% 的穩定幣 (Stablecoin) 轉換成 BNB。” 智能體會根據你的資產規模自動選擇最佳策略。如果金額較大,它會分階段完成;如果金額較小,它可能會直接用市價訂單完成。這些事情會在後臺自動完成,而我們只需要設定目標。
Chamath:你覺得現在有哪些加密貨幣項目可能適合智能體使用?
CZ:
你是說理論上智能體可以使用的加密貨幣嗎?現在還處於早期階段,我不想做過多的推測,也不想具體提到某些項目的名字,因為這可能會導致代幣價格波動。但我知道,目前有不少人在研究這個領域,尤其是最近關於 AI 智能體和社交網絡的結合,已經引起了越來越多的關注。
我相信,我們最終會實現這個目標。
Chamath:對我來說,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如果你問我是不是一個比特幣的極端支持者 (Bitcoin Maximalist),我會說不是。儘管我很早就接觸了比特幣,但我認為它有兩個主要問題:一是缺乏可互換性 (fungibility),這對實現大規模應用是個障礙;二是缺乏隱私功能。我認為隱私問題可能是限制比特幣普及的最大因素之一。
你覺得隱私在加密貨幣中扮演了什麼角色?
CZ:
我認為隱私在我們的社會中是一個非常基礎的需求,但正如你所說,比特幣和大多數加密貨幣目前確實缺乏足夠的隱私功能。當比特幣被設計出來時,它被認為是“偽匿名的 (pseudo-anonymous)”,但實際上,區塊鏈上的每一筆交易都是公開的。任何人都可以查看和追蹤這些交易的記錄,尤其是現在有了帶有 KYC 功能的中心化交易所,這讓追蹤變得更加容易。
Chamath:
沒錯,而且人們總是用同樣的論點來反對隱私:有人可能會利用加密貨幣進行非法活動。我承認確實有這樣的情況,但絕大多數情況下,人們只是用它來做一些普通的事情,這些都是個人的選擇,不應該受到外界的評判。相比之下,美元是完全可互換的,它具有完全的匿名性,我們根本不知道手裡的美元在之前被用來做過什麼。
CZ:
是的,實際上有一些場景中,隱私是至關重要的。比如說,如果你預訂了一家酒店,而別人通過區塊鏈知道了這家酒店的收款地址,他們就可以推測出你會住在那裡。這對你的個人安全來說是一個很大的風險。
這也是為什麼人們不會隨意在網上公開自己的家庭地址,在一些國家公開別人的家庭住址甚至是違法的,所以隱私確實有非常實際的應用場景,然而目前比特幣和大多數加密貨幣並沒有提供足夠的隱私保護功能。
當然,也有一個反對的觀點:執法部門希望能夠追蹤犯罪分子。但實際上,即使沒有隱私功能,追蹤犯罪分子也是可以做到的。我支持打擊犯罪,但我們仍然需要解決隱私的基本問題。
我認為,在未來,我們整個行業需要找到方法來改進隱私功能。目前幾乎沒有人真正關注這個問題,雖然確實有一些專注於隱私的加密貨幣項目,但它們的市值和規模都很小,還沒有形成足夠的影響力。
Chamath:你寫書的進展如何?你寫這本書的初衷是什麼?是為了抒發情感,還是為了表達某種觀點,或者是為了講述你的故事?
CZ:
其實都有一點。這本書的起點很簡單——我當時在監獄裡很無聊,所以就開始寫書。當時只是為了讓自己忙起來,不想總是和其他人聊天,我用一個非常簡陋的終端打字,然後把內容發給我的助理。
等我出獄後,我發現自己已經寫了不少內容了,於是覺得如果再花點時間,就可以把它整理成一本書。不過,編輯一本書真的非常耗時,每次修改都需要兩到三週,因為這本書現在大概有 95,000 字,差不多 300 頁,而且我還在同時編輯英文版和中文版,這讓整個過程變得更長了。
至於寫這本書的目的,我覺得最主要的是想把我的故事講出來,我覺得外界對我有很多誤解,包括對我個人、對 Binance,甚至對整個加密貨幣行業的誤解。
關於加密貨幣的負面報道很多,關於 Binance 和我的負面報道也不少。甚至還有一些關於特朗普和共和黨的負面報道。當然,這些內容在我的書裡不會太多提及,我只是想通過這本書,讓人們更好地瞭解我是誰,以及從我的角度來看,Binance 是一家怎樣的公司。
Chamath:你認為這對你的孩子來說是一個重要的故事嗎?
CZ:
我想是的,他們當然更多站在我這邊。他們知道很多媒體的報道並不完全屬實,但坦白說,我沒有足夠的時間向他們逐一解釋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所以,我希望通過這本書,能夠讓他們瞭解更多的細節,雖然這本書不可能涵蓋所有的內容,但我儘量把能說的都寫進去了。
Chamath:你對你的孩子有什麼期望?
CZ:
我希望他們能夠過上健康、幸福的生活,無論他們如何定義幸福。如果他們覺得做一個普通人就很開心,那對我來說很好;如果他們想創業,建立公司,那也很棒;如果他們想從事藝術創作,或者投身人道主義事業、慈善活動,那也很好。不管他們選擇做什麼,我都希望能支持他們。
Chamath:這和你父母對你的期望有多相似或者不同?
CZ:
其實很相似,我父母對我並沒有施加什麼壓力。他們從來沒有要求我必須成為什麼樣的人,我的父母對我說的很簡單,也很“非典型中國式”。他們告訴我:“不要傷害自己,也不要傷害別人。” 不要吸毒,不要犯罪,不要做傷害別人的事情。這就是我從他們那裡得到的所有教育。
Chamath:
我們經常會把成功描繪成一種遙不可及的東西,好像只有極少數人才能做到,但實際上事實並非如此。
CZ:
是的,我就是一個普通人。
Chamath:
是的,很多人也對我這樣說,他們會覺得有些難以置信,“你真的只是個普通人。” 我一直認為,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是非常重要的。當你全身心投入到自己熱愛的事情中時,時間會過得飛快,你會情不自禁地想去嘗試,去學習新的東西,這種持續探索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樂趣。
CZ:
當然,我首先要說,我真的只是個普通人。我知道自己並不是超級聰明的人,但我也明白,成功並不需要你成為天才,你當然不能太笨,但也不需要特別聰明。成功更多取決於其他因素,這些都會對成功起到重要作用。當然,運氣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改變周圍的環境是非常困難的,所以唯一能改變的就是自己。我的建議是,每天稍微努力一點點就好,不需要逼自己太緊,因為那樣會讓你筋疲力盡,反而無法堅持下去。找到一個平衡點很重要,要確保這種狀態是可以長期維持的。如果你能這樣堅持 30 年,再加上一點點運氣,你很可能會取得相對的成功。也許你不會成為億萬富翁,但你一定能過上相對舒適、無憂無慮的生活。
Chamath:你覺得是否有必要打破一種神話,也就是“成為億萬富翁並沒有看上去那麼美好”?
CZ:
當然。其實錢就是錢。如果把人生比作一張蜘蛛網圖,金錢只是其中的一條線。一旦你有了足夠的錢,更多的錢並不會讓你更快樂。真正讓人感到幸福的,是健康、家庭,以及那些讓你感到滿足的事情,這些內在的成就感,才是讓人真正感到幸福的源泉。
這些方面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有時候你會賺得多一些,有時候少一些,但真正關鍵的是,你的健康狀況如何?你是否有足夠的時間陪伴家人?你是否能夠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你是不是在做自己真正熱愛的事情?你是否和你想要在一起的人共度時光?如果你的家人都健康,那已經是莫大的幸運了。
此外,心理健康同樣非常重要。如何管理壓力,如何保持內心的平靜,這些都是需要關注的。很多人一味追求金錢,卻往往犧牲了其他一切。他們工作得非常辛苦,幾乎沒有時間陪伴家人,也難以抽出時間照顧自己的健康。等到 10 年或 20 年後,他們的身體可能已經被透支,健康大不如前,即使他們擁有了鉅額財富,卻已經沒有精力去享受生活了。
這也是為什麼我現在特別感激不用再管理 Binance 了。過去管理 Binance 的那段時間,確實是一段非常愉快且充滿成就感的經歷,但同時也讓我在其他方面有所忽視,比如個人生活和健康。我現在有了更多的時間,可以把精力放在其他重要的事情上,雖然我非常珍惜那段經歷,但現在我感覺自己找到了更好的平衡點。
歡迎加入深潮 TechFlow 官方社群
Telegram 訂閱群:https://t.me/TechFlowDaily
Twitter 官方帳號:https://x.com/TechFlowPost
Twitter 英文帳號:https://x.com/BlockFlow_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