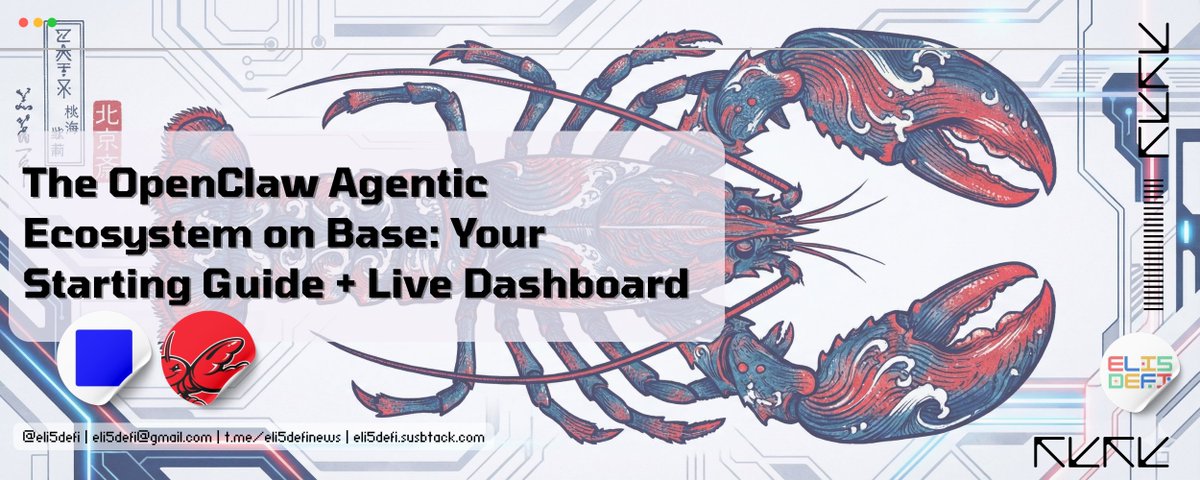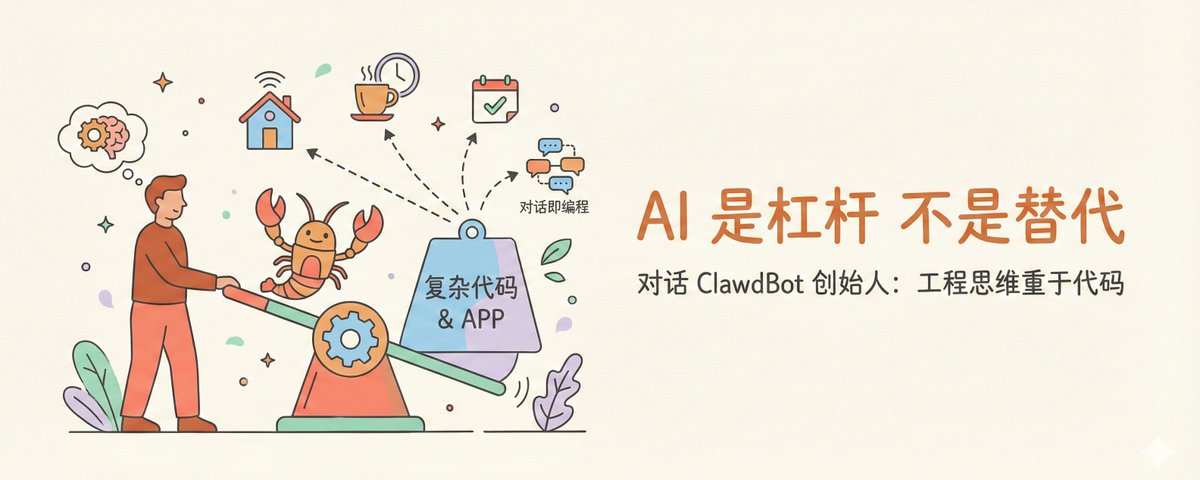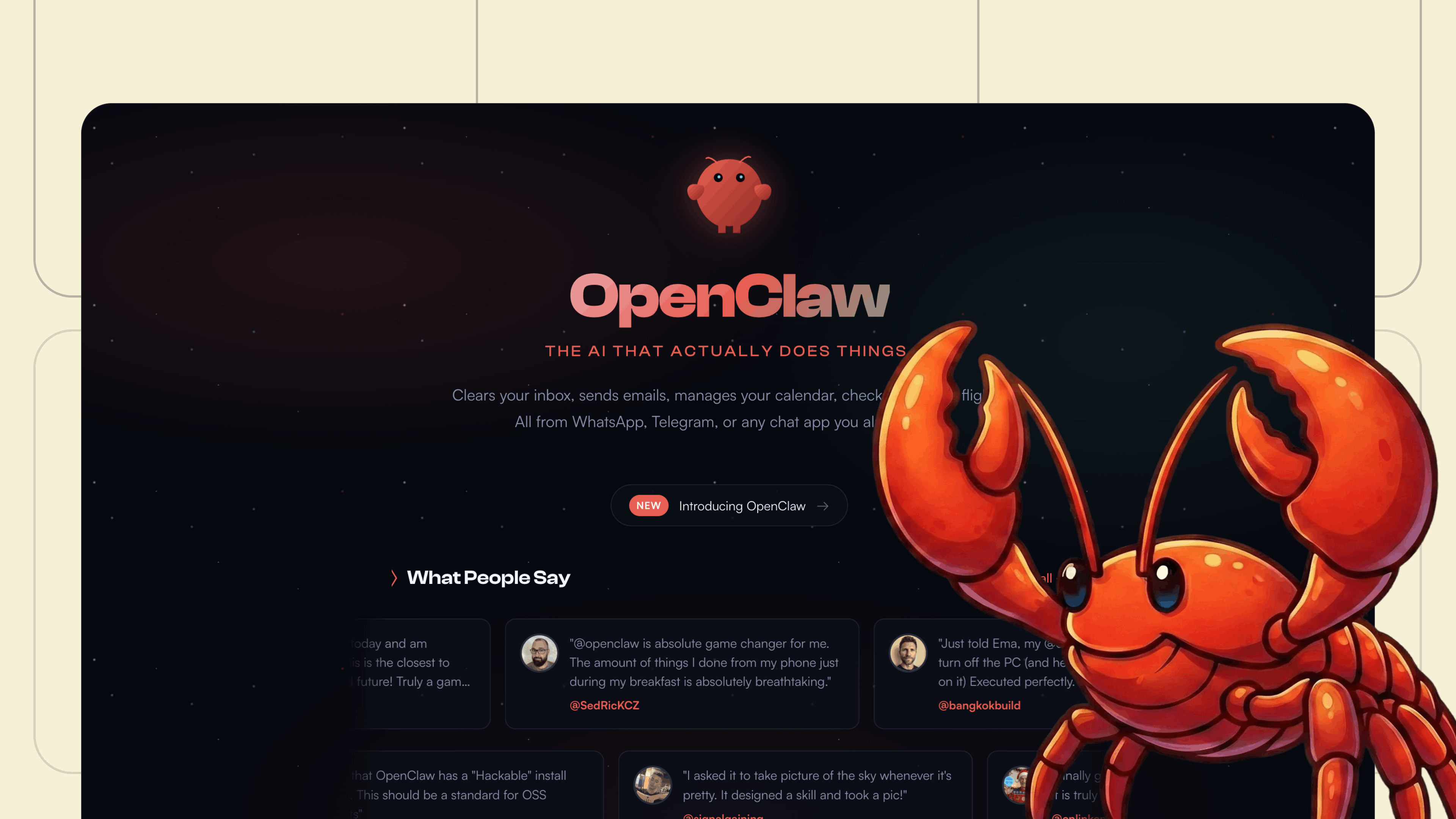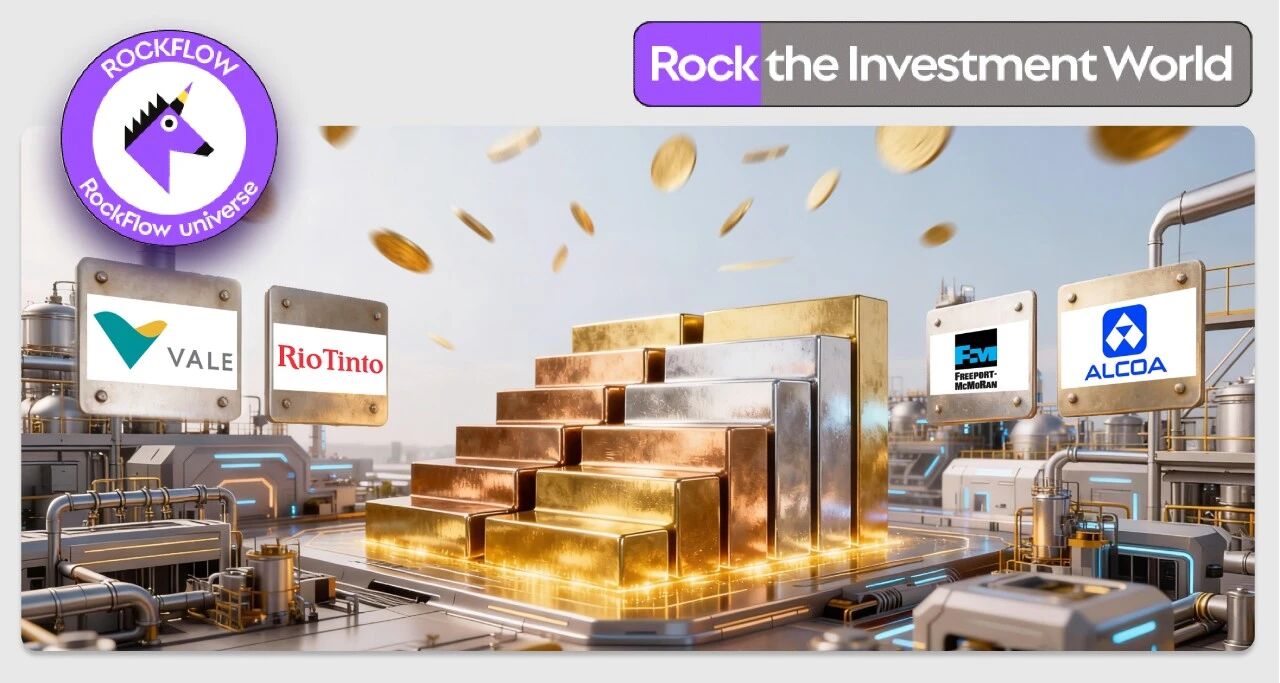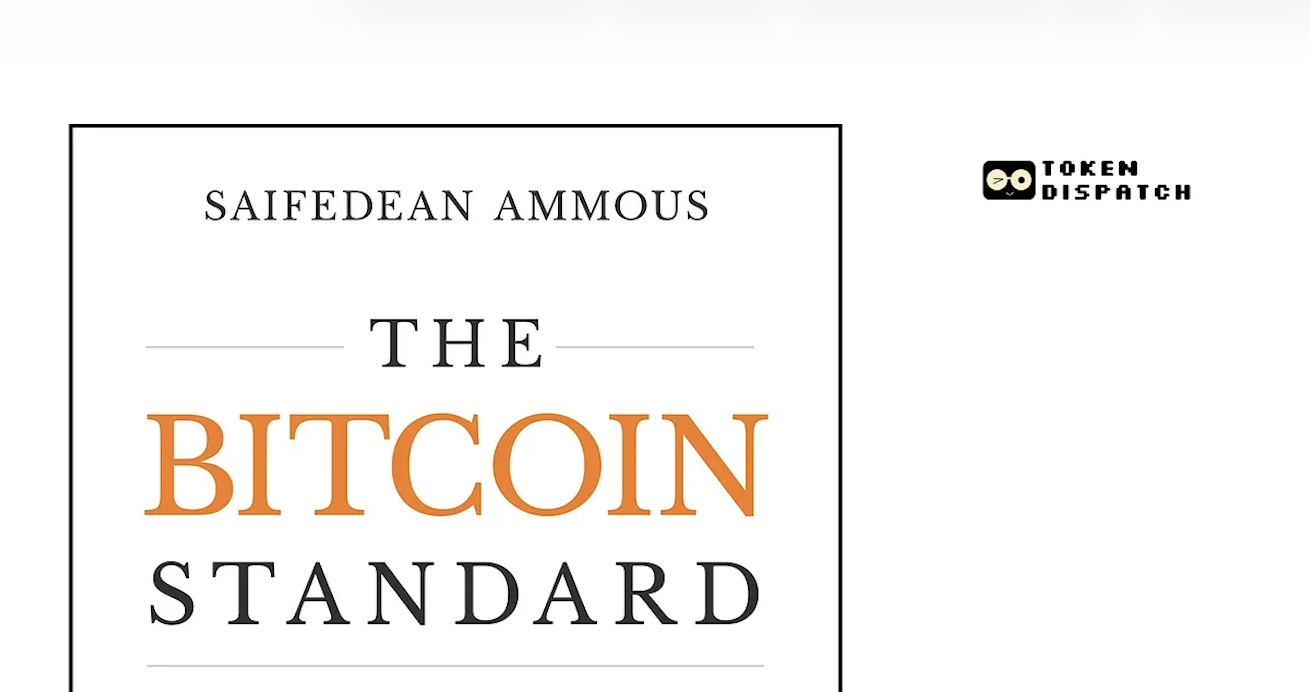對話 DINQ:我們要用 Agent 終結 AI 行業的信息差,讓身價明碼標價
TechFlow Selected深潮精選

對話 DINQ:我們要用 Agent 終結 AI 行業的信息差,讓身價明碼標價
在 DINQ 測完身價我破防了,姚順雨值 1000 萬美金,而我只值 1000 塊底薪。
在 AI 圈,如果你還沒被 DINQ “羞辱”過,那你可能還沒真正入圈。
這個產品的走紅方式極其“離譜”:它不僅能給人才開出令人心動的 Offer,還自帶一個毒舌屬性爆表的 “AI 辣評” 功能。只要你敢把 GitHub 鏈接或谷歌學術主頁丟進去,AI 就會化身嘴臭面試官,對著你的引用量和代碼貢獻精準開炮。

通過分析姚順雨的 Paper,Citation、工作經歷和教育背景,DINQ 給出了 1000 萬美元的預測薪資
這種“求捱罵”的自虐心理,意外地統一了全球科研人的社交戰線。從斯坦福的實驗室到硅谷的咖啡館,到處都是轉發自己身價截圖的人。當姚順雨被測出 1000 萬美金身價,並被拉出來和另一位比武時,這個只有 8 個人、剛剛拿到藍馳數百萬美元投資的小團隊,已經悄悄潛入了全球頂尖 AI 人的社交雷達。
調侃學術新星,辣評姚順雨。
“順雨的引用次數增長速度簡直比火箭還快,他大概是專門寫了個‘語言智能體’,每隔三秒就自動引用一次自己的論文。憑藉 25 的 H 指數和 21,000 次引用,他成了普林斯頓大學唯一一個‘參考文獻列表長城還要長的人。”

調侃學術泰斗 Jitendra Malik。
“憑藉 185 的 H 指數和超過 25 萬次的引用,Jitendra 已經達到了學術成名的頂峰——他基本上是每個計算機視覺博士生文獻綜述裡的‘終極 BOSS’。我甚至懷疑他現在根本不需要投稿了,他只要在 GPU 旁邊打個噴嚏,那兒就能自動蹦出一篇年度最高引論文。”

辣評跨界大佬比爾·蓋茨。
“比爾·蓋茨,哈?唯一能把賣窗戶錯誤變成十億美金生意的人!作為‘首席執行官’,你已經掌握了讓人們相信你是真材實料、同時還能巧妙躲過所有軟件更新的藝術。記住,夥計,在澳大利亞,連袋鼠都想跳過你的‘遺產’!”

搞笑歸搞笑,也有諸多大佬在內測階段便加入了 DINQ,不乏 OpenAI 的各類研究員。甚至還有不少大佬在 X 上主動安利 DINQ。


但玩梗背後,DINQ 正在幹一件挺嚴肅的事。
在創始人 Sam 和 Kelvin 看來,領英這種靠關鍵詞匹配的搜索模式,在 AI 時代已經“老掉牙”了。真正的 AI 大神往往是“隱形”的:他們不投簡歷,不混職場社交,他們的靈魂散落在 arXiv 的論文裡、Hugging Face 的項目裡,甚至 Twitter 的深夜吐槽裡。
DINQ 的邏輯是:既然你不出面,我就用 AI Agent 像偵探一樣去“人肉”你。它不再是生硬的查戶口,而是具備了理解技術邊界的能力。哪怕 HR 的需求模糊到“找個能解決視頻生成人物一致性的年輕人”,Agent 也能瞬間從全網碎片的痕跡中,揪出那個從未出現在人才市場上的“水下”天才。
在這場近兩萬字的深度對話中,他們聊的不只是如何幫大廠挖人,而是如何通過“Less Structure, More Intelligence”的技術哲學,為全球上千萬 AI 開發者打造一張通往未來的DINQ Card。
一個建築系研究生的激進轉型,靠自學敲開達摩院的大門
Jane:先用一句話簡單介紹一下你自己和公司。
高岱恆 Sam:DINQ 是一個面向 AI 開發者、研究員與創造者的人才智能平臺。我們通過自動化分析個人的真實成就與影響力,幫助他們更高效地被世界級機會發現與連接。至於我個人,我是第一個通過開源貢獻進入阿里達摩院(後來通義實驗室)的算法工程師。
Jane:我看你的履歷,最初好像並不是計算機專業?你是從什麼時候決定轉軌的?畢竟你後來的職業生涯幾乎都是圍繞這個核心展開的。
高岱恆 Sam:對,我本科其實是學建築的。真正意識到並主動轉向計算機是在 2017 年。當時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時代背景——國內正處在第一波比較狂熱的 AI 創業浪潮中,一方面機會非常集中,另一方面互聯網上可獲取的學習資源也第一次變得足夠豐富,這讓“非科班轉入 AI”在現實中變得可能。
但對我個人來說,更本質的原因並不是“追風口”,而是我在原來的發展路徑上已經明顯感受到走不太通了。當時我在北京工業大學讀研究生,如果繼續沿著那條路走,想在北京找到一份月薪一萬左右的工作都非常困難,而且往往伴隨著強度極高、長期不可持續的加班。
同時,那個階段我也已經能接觸到一些行業內部的判斷,很多人都在討論:當時的發展結構其實並不健康,尤其是房地產相關的長期預期並不樂觀。在這樣的背景下,我開始比較早地問自己一個問題:如果這條路註定會“GG”,我是不是應該主動跳出來?
所以最終,我是把對時代趨勢的判斷和對自身處境的反思結合在一起,做了一個相對激進但理性的選擇——開始系統性地在互聯網上自學 AI 和計算機相關的課程,這也成為我後面所有事情的起點。
Jane:轉型計算機領域,你當時的切入點是什麼?
高岱恆 Sam:主要是通過吳恩達老師的公開課進行系統性學習。我覺得這個行業本質上也沒有教科書,大家都是在基於現有資料去學習的這麼一個過程。所以在這個行業裡,你的出身和背景沒那麼重要,反而是你對這個領域的興趣更重要一點。
Jane:聊聊你職業生涯中那個非常受認可的項目吧,就是你在阿里達摩院期間做的那個?不過我想確認下,去阿里是你決定深耕 AI 和算法領域的第幾份工作?
高岱恆 Sam:首先我糾正一下,這個項目不是我在阿里做的。阿里是我第二份工作。我講一下脈絡:我 2018 年畢業之後,其實畢業之前我就一直在做開源項目了。最開始做開源,是給像 TensorFlow 這樣的深度學習框架寫代碼。
但那個時候我發現一個問題:當我做這種偏底層的東西時,其實很少有人能理解“這是你做的”或者“你具體做了什麼”。在那個年代,這事很難被理解;但也有好處,比如因為我有這些貢獻,所以當時像 OneFlow 袁進輝老師他們這種做深度學習框架的國內團隊就會知道。因為那時候能在 TensorFlow 和 PyTorch 上有超過十個 PR、並且在大陸工作的,其實不太多。
然後我就在想一個問題:我能不能做一些不那麼底層、所見即所得的東西,讓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幹什麼的,我也不需要費心解釋。因為我過去有相當於藝術方面的背景,所以我就想說,做圖像或者視頻方向可能更容易讓別人理解我在做什麼。
所以畢業之後,我最開始去了一家小公司。在公司工作之餘,我基本每天都在做開源項目——DeepFaceLab 也是在那個階段搞的。
Jane: 這個項目後來反饋極好。當時是你一個人單打獨鬥,還是有團隊一起?
高岱恆 Sam:其實是一個跨國開源協作項目。我記得當年的影響力排名,它好像僅次於 TensorFlow 排在第二。
Jane: 這麼高影響力的項目,當時沒想過投頂會論文嗎?
高岱恆 Sam:投過,但被拒了。原因是內容在當時極具爭議和敏感性,學術界不敢冒這個風險。後來我也沒再糾結,直接掛在 arXiv 上公開發表了。
Jane: 這個項目的正反饋,是不是堅定你後來選擇達摩院的信心?當時為什麼沒考慮 Meta 或者字節這種大廠?
高岱恆 Sam:核心原因在於達摩院能讓我繼續深鑽視頻方向。當時 Meta 給的 Offer 是“紅組(Red Team)”,主要負責防禦性內容審核,每天要處理大量負面視聽素材,我覺得對身心健康不是很好。而當時的字節更多是音視頻編解碼方向,跟我垂直的研究領域相關度不高。
Jane:達摩院確實更偏前沿技術研發。你在那裡做了不少數字人的項目,能分享下那段經歷和它帶給你的思考嗎?
高岱恆 Sam:在達摩院的兩三年裡,我們做了很多從技術到落地的嘗試。比如 2022 年虎年春晚,我和同事駐場開發了一個 3D 小老虎數字人,登上了央視網絡春晚直播。後來又參與了冬奧會的 3D 數字人項目。 再後期,我轉向了基於擴散模型的圖像生成,其中最成功的是虛擬試衣項目Outfit Anyone。這個項目目前每年能為阿里雲創造一兩億元的營收。
Jane: 你在達摩院期間,正好完整見證了 ChatGPT 爆發前後的行業鉅變。當時內部的氛圍是怎樣的?我聽阿里的朋友八卦過,早期大模型在國內大廠內部的地位似乎有些微妙。比如 21、22 年雲棲大會時,楊紅霞老師原本好像不是講大模型的首選,是臨時頂上去的。我很客觀地好奇,你在內部感受到的真實變化是什麼?
高岱恆 Sam:確實,不過首先要說明的是,我們組和他們(楊紅霞老師團隊)不在一個序列,他們更偏文本大模型。我是 2020 年進公司的,像羅福莉、林俊暘這些後來在大模型領域很活躍的研究員,也都是 2020 年前後進來的。我身邊有不少“阿里星”朋友,所以對當時的情況比較瞭解。
其實關於大模型和人才的價值,今年扎克伯格的一些動作算是把這件事徹底“敲死”了(蓋棺定論)。你看現在大廠願意砸重金挖的人,大多是那些真正做出過核心技術的年輕人。
Jane: 確實,技術話語權正在迴歸年輕人手中。
高岱恆 Sam:沒錯。我覺得這背後的邏輯很有意思——原本很多研究成果是分散在各個社區和論文裡的,但現在大家開始意識到,誰能把這些分散的成果集合起來並實現突破,誰才是核心。
Jane:我們回到達摩院的機制:當時你們如果有一個 idea 要落地,內部流程是怎麼樣的?考核指標是看論文,還是看業務價值?
高岱恆 Sam:達摩院當時的內部流程非常“自下而上”。組長通常只會劃定一個宏觀的研究方向,剩下的全靠我們自己去探索,管理上非常扁平,基本沒有什麼細碎的約束。如果你需要資源——無論是算力、數據標註還是實習生——都可以去申請調動。
在 21、22 年那個階段,大家其實還在摸索期,不知道大模型的終局在哪,所以那時候“看論文、找靈感”是常態。
Jane:懂了。所以那時候並沒有那種“硬性發稿量”的 KPI 壓力,對吧?不像商湯早期會有非常明確的論文指標。雖然大家都是研究型組織,但阿里的底色似乎更自由一些。
高岱恆 Sam:是的,確實如此。這種自由度給了技術探索很大的空間。
Jane: 那你是什麼時候正式萌生創業想法的?是做了那個開源社區之後,就開始覺得“我得出來闖闖,雖然方向還沒完全定死”?
高岱恆 Sam:沒錯,確實是那個階段開始成型的。
Jane:那你當時為什麼決定離開達摩院?是想先以開源方向作為探索,還是有別的考量?而且你和合夥人後來碰撞出的這個產品形態,是誰先提出的雛形?
高岱恆 Sam:最開始我們確實有過一些務虛的討論。我當時堅信一點:新一代的、尤其是吸引年輕人的職場社區,絕對不能再走“貼簡歷、曬學歷”的老路了,得有點不一樣的玩法。但說實話,那時候我倆討論了半天也沒理出個一二三來。
今年年初,我一直待在美國。當時的思路比較簡單:我先嚐試用 Cursor(AI 代碼編輯器)做點 Vibe Coding,搞個好玩的小應用投石問路。這個應用的核心邏輯很精準:用戶輸入名字或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鏈接。
我太瞭解這群搞研究的年輕人了——進實驗室的第一件事往往就是打開谷歌學術,看自己的引用量漲沒漲。
Jane: 抓住了科研人的痛點。
高岱恆 Sam:沒錯。我做的功能就是:你把鏈接粘過來,AI 給你來個“辣評”。比如調侃你“一作數量不夠,還得努努力”,或者“怎麼總是不發頂會”之類的,主打一個幽默好玩。這個開發成本極低,但上線後我們有兩個意想不到的發現:
第一,模型具備推理能力後,它能根據一個人的成就給出非常精準且抽象的評價,甚至能把人“噴”得很到位。我發現大家竟然非常喜歡聽 AI 噴自己,那種“求捱罵”的心理很有趣,反而誇獎大家覺得沒勁。
第二,這個小東西跑通後,我發現它能延展的空間異常廣闊。正是基於這個“辣評”工具的反饋,我們才開始深度碰撞,最終打磨出了現在的產品形態。
Jane:明白,是從一個極小的正反饋里長出來的。很有意思。
紅杉的人才招聘困境,讓 Kelvin 看到 AI 時代招聘的結構性缺口
Aaron:Kelvin 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孫辰昕 Kelvin:我的經歷比較純粹,職業生涯一直深耕在 HR 和招聘領域。比較特別的轉折點是機緣巧合加入了紅杉資本,負責內部投資人的招募,包括科技和消費賽道的年輕人才。 從紅杉出來後,我嘗試過幾次創業。第一段創業其實和我們現在的業務邏輯很像:當時正值小程序爆發,我敏銳地感覺到微信生態(朋友圈、群聊)的招聘效率正在超越獵聘、Boss 等傳統平臺,於是做了一個招聘小程序。
Aaron: 那次嘗試的結果如何?
孫辰昕 Kelvin:比較戲劇性。產品上線一週,疫情就爆發了。雖然線上增長非常驚人——B 端有上百家公司在群裡自發擴散,兩週內就湧入了 10 萬份簡歷,但融資環境跌入冰點。當時大家還不習慣線上會議,我連投資人的面都見不到。苦撐幾個月後,那次創業無疾而終,成了我很大的遺憾。之後我涉獵過跨境電商,但最終還是繞回了自己的“主賽道”。
Aaron: 很多人好奇,紅杉招募年輕投資人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孫辰昕 Kelvin:要求每年都在變,但核心邏輯只有一句話:“同齡人中的絕對佼佼者”。這聽起來抽象,但反饋到感官上就是:一個 25 歲的人,一眼看去就要氣場不同。我們不限背景,記者、產品經理、程序員都可以。只要你具備極強的深度思考能力和自驅力,能明顯拉開與同齡人的差距,就是我們要找的畫像。
Aaron: 站在 HR 的視角,消費或科技公司招人的核心難點在哪裡?
孫辰昕 Kelvin:幫 Portfolio(被投企業)招人,最大的難點其實是“沒名氣”。不管背後站著紅杉還是高瓴,大多數候選人根本不知道這些公司是做什麼的。品牌認知度低,是招聘中最大的障礙。
相比之下,To C 公司就好招得多,因為他們天天打廣告。我印象很深,比如給拼多多介紹人就非常順暢,因為大街小巷都是那首洗腦魔曲。上市前全上海鋪天蓋地都是拼多多的廣告,知名度在那擺著。但 To B 領域,甚至是一些大家聞所未聞的前沿方向,想要實現人才突破極其困難,因為外界根本沒人知道它。
Aaron: 從產生需求到最後發出 Offer,大概需要經過多少環節,耗時多久?
孫辰昕 Kelvin:常規來說,首先是全渠道搜索:線上平臺掃一圈,從國內外的招聘網站到發朋友圈、群聊動用人脈,甚至去聯繫那些“認識目標人才”的人,尋找關鍵的流量節點;奢侈一點的就找獵頭。總之,所有渠道都會試一遍。
大概一到兩週時間,能篩掉不合適的人,沉澱出三到五個畫像(Profile)完整、且聊下來意願度(Motivation)不錯的候選人。到這一步兩週就過去了。接著安排面試、談 Offer,順利的話也得一兩個月才能敲定。再加上入職準備期,可能又是三四個月。也就是說,招一個難搞的崗位,即便在順利的情況下也要花掉一個季度;而很多崗位甚至是“無解”的,永遠也招不上來。
Aaron: 從你的專業角度出發,你會怎麼用一句話來描述 DINQ 的業務?它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產品?
孫辰昕 Kelvin:如果拋開 AI 的技術外殼,我認為它是所有 AI 從業者最高效表達自己的工具。你看我們的個人主頁,其實就是一種高效率的自我表達方式。
從招聘方的角度看,我們的搜索引擎是更高效率的人才搜索引擎。它基本上能直接替代我剛才說的前兩個步驟,幫招聘從業者至少節約兩週的盲找時間。
Aaron: 你是什麼時候意識到,在 AI 這個新賽道里,傳統的投遞簡歷、領英 Profile 以及傳統招聘流程已經失效,需要被顛覆了?
孫辰昕 Kelvin:雖然這幾年我沒直接做招聘,但我身上一直貼著“能幫人招人”的標籤。身邊一些 AI 賽道的新興創業者還是會找我問:Kelvin,能不能幫我介紹幾個厲害的算法工程師或全棧開發?
在那一刻我發現自己“失靈”了。以前通過一度、二度人脈介紹人才很容易,但 AI 這波浪潮興起後,我發現圈子裡的人我一個都不認識。這讓我感到很焦慮:雖然我不直接幹這行了,但我不想失去這個專業標籤。
我意識到出現了一波全新的人群。我認識很多傳統領域的 CTO,但他們不涉及這個領域,也弄不懂這套邏輯。現在已經不是那種“只要給 200 萬年薪,找個傳統 CTO 就能解決 AI 技術攻關”的時代了。像 Sam 這樣的人才,以及市面上很多頂尖的年輕人,他們遊離在傳統視野之外,我們甚至不知道他們在哪裡,這就是我當時的困境。
Aaron: 為了解決這個困境,你做了哪些嘗試?
孫辰昕 Kelvin:我開始研究他們究竟出現在哪裡。我也去請教大模型公司的 HR 朋友:你們到底去哪找人?結果發現他們居然要去 GitHub、谷歌學術(Google Scholar)里人肉搜索,在領英上反而很難找到人。即便找到了,還得去個人主頁翻聯繫方式發郵件。業內推薦效率也低,雖然能解決一點問題,但總之都是在通過“非傳統渠道”找人。於是我也學著這套路子去找。
Aaron: 所以可以理解為,正是因為你覺得原有的找人方式太低效,才想到要做現在這個產品?
孫辰昕 Kelvin:是的。但坦白說,這個產品不是我“做”出來的,是 Sam 做出來的,是他讓我意識到“原來這個問題可以這樣被解決”。在這方面我是後知後覺的。
Aaron: 你們兩位最初是怎麼結識的?
孫辰昕 Kelvin:說來也很簡單。當時有位朋友委託我尋訪一個既懂交易(Trading)又懂 AI Agent 的跨界人才。我注意到一個非常有名的項目,就是 Sam 剛才提到的那個 OS。我在 Paper(論文)上看到作者裡有一箇中國名字——“高岱恆”,於是就開始動用所有資源,尋找可能認識他的人。後來通過一家投資機構的投資人牽線,才正式結識了 Sam。這其實還是我的“老手段”——通過招聘積累下的深厚人脈。
Aaron: 當時對 Sam 的第一印象如何?後來產生了什麼變化?又是什麼契機讓你決定和他一起共事?
孫辰昕 Kelvin:坦白說,最初並沒有什麼特別深刻的第一印象。那段時間我聯絡了很多類似的技術大牛,基本就是例行公事的溝通:我手頭有個機會,你考不考慮?而他當時理所當然地拒絕了我。
起初,我對他個人以及 AI 領域的認知都沒那麼深。轉折點發生在後來,他萌生了做招聘產品的想法,發現我在這方面比較專業,便反過來找我進行深入交流,我也才慢慢對他有了更清晰的認知和感覺。早期我們一直是線上溝通,雖然沒見過面,但非常聊得來。
我發現他為了把事情做成,會展現出一種極廣泛的學習姿態。他聽說我懂招聘,就追著問了許多非常硬核、細緻的業務問題。後來果不其然,我得知他是跨行自學 AI 出身的。我認為一個人的自學能力一旦足夠強,就會演變成一種底層習慣,從而在方方面面實現突破。所以我後面對他最核心的標籤評價就是:擁有極強的自學能力。
高岱恆 Sam:感謝 Kelvin 的肯定。當時我的想法很簡單:那個項目收尾後,我還想再探索些新東西。在盤點我們各自擅長的領域和底層能力時,我發現我們對“人”的特質、認知以及流動規律有著很深的理解。我就在想,能不能圍繞“人”這個核心去做?
一旦確定了這個基點,最自然的延伸就是招聘領域,而且當時市場的需求缺口確實巨大。基於這個初衷,我就向 Kelvin 多請教了一些。最開始交流時我還在美國,Kelvin 分享了很多他對人力資源行業的深度認知。隨著聊得越來越透,我們都覺得可以一起把這件事做大。
Aaron: 所以你們一開始就對大方向達成了共識,而具體的產品形態是你們兩人不斷“碰撞”出來的?
高岱恆 Sam:是的。關於產品形態,我現在不敢用“收斂”這個詞,因為我認為在目前的 AI 階段,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宣稱自己的平臺產品已經完全定型了。如果技術和模式真的已經“收斂”,大家也就不需要花費數億年薪去爭搶那些頂尖的華人研究員了。
在行業尚未定型的背景下,我們實現了階段性的形態共識:我們認為目前的模式更符合年輕人的直覺。至於它是怎麼演化出來的?其實沒有捷徑,就是因為我們與年輕人、與目標用戶群體的接觸最緊密、最頻繁,所以我們最清楚他們真正喜歡的是什麼。

楊建朝 vs. 周暢
產品拆解:DINQ 如何用 Agent 推理終結 AI 人才的搜尋困境?
Aaron: 傳統招聘核心是關鍵詞匹配,DINQ 的人才評估體系有哪些維度?與傳統框架相比,本質區別在哪?
高岱恆 Sam:從技術角度看,我們正處在一個“解構與重組(Remix & Decouple)”的時代,信息複雜度呈幾何倍數增長。這導致了一個典型矛盾:一個候選人的核心標籤可能是“R2”或“拉網”這種模型,但 HR 的查詢詞可能是“圖像大模型”或“視頻生成”。在領英這種 Lexical Search(關鍵詞匹配)模式下,只要詞對不上,這個人可能一輩子都搜不出來。
而且我們調研了 OpenAI 一千多名研究員,發現超過一半的人根本不維護領英,甚至沒有賬號。技術大牛的信息往往散落在官網博客或二開的論文裡,B 端找人極難。
Aaron: 所以你們的解法是?
高岱恆 Sam:既然渠道如此碎片化——他可能在 Hugging Face 攢了個項目,在 Twitter 發了技術解讀,在 arXiv 發了文章,又在小紅書發了頂會 Poster 合照。我們決定放棄以“領英 Profile”為核心的路線,轉而構建一套以Agent 調用為主的系統。我們提前對頂會、AI 公司做大量數據預處理和 Embedding(向量化),當用戶查詢時,Agent 會實時調取全網信息進行 Reasoning(推理)。
例如,Sora 2 的一作華人叫李流年(Harold),你問傳統的通用大模型或 Agent 平臺,基本搜不出來,因為數據沒對齊。但我們的系統能根據他的論文、GitHub 和社交媒體動態,把他精準抓取出來。
Aaron: 我想深入聊聊“碎片化”的問題。傳統招聘極度依賴領英(LinkedIn),但 AI 研究員和工程師的信息往往分散在 Google Scholar、GitHub 等平臺。你能舉個具體例子,說明這種碎片化嚴重到什麼程度嗎?
孫辰昕 Kelvin:現在的痛點在於,當 HR 拿到需求時,業務方對年輕算法研究員的要求已經具體到了極端,比如要解決“視頻生成中的人物一致性”這種極其細分的命題。HR 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根本不知道這群人在哪。
我們的工具允許 HR 把手中掌握的碎片化信息全部丟進來,先解決“從 0 到 1”的突破。在過去,僅靠隻言片語去領英搜,大概率一個都搜不出來,因為沒人會把具體的科研成果放在領英上。這是領英最大的硬傷——上面往往只有學校背景,信息密度太低。
如果你只是要招“清華北大”的學生,領英尚可應付;但如果你要找能解決某個具體技術難題的人,目前行業內的技術叫法甚至都沒統一,領英肯定搜不到,Boss 直聘或獵聘更是不可能——目標人群壓根不會去那些地方求職。這在以前幾乎是“無解”的。
傳統的笨辦法是去打聽、去硬啃論文,但要求 HR 去讀論文既不現實,也不是他們該乾的事。最終只能靠口口相傳的打聽或內推,效率極低。
Aaron: 如果我是 Meta 的 HR,想招一名 AI Scientist,在 DINQ 上的典型流程是怎樣的?
高岱恆 Sam:我們提供三種模式:
第一,你明確有需求,直接一段話丟過來,比如“我要在 NeurIPS 2025 的 oral 裡找做某方向的人,最好有美國工作簽證”。
第二,你已經有 JD(比如在 Greenhouse 這類平臺上),把 JD 扔過來就行,系統幫你找人。
第三,你已經有一個人,比如 A 很合適但不來、或 A 是你員工,你可以問“給我找一個類似 A 的人”,比如還在讀博、或者積極看機會。也可以問“找從字節跳動出來的 95 後,在某方向有建樹、可能看機會的”,甚至“去 SCI 找這樣的”。都可以。
孫辰昕 Kelvin:我補充一下。過去找人如果是標準流程,專業 HR 或最貴的獵頭公司會先做廣泛 sourcing,做完組成 100 人的 long list。然後聯繫、排除,主要確認兩件事:能力和意願。兩者都符合才推進。之後形成 short list 給 hiring manager(基金合夥人、CTO 等)。
我們現在相當於一步直接出 short list,因為前面的全網 sourcing 基本由 agent 做了,不需要人再花時間。產出就是 short list。然後人就應該去做自己最擅長的事:直接溝通、說服對方。
Aaron: 我發現你們有個給候選人“開身價(Package)”的功能,甚至吸引了斯坦福、伯克利、紐約大學的很多教授主動體驗,這是怎麼生成的?我自己給姚順雨測了一下,他是 1000 萬美金的 Package。
高岱恆 Sam:我們利用 Level.fyi 等公開數據,對人才的職級和身價做了一個打分模型。原本是做著好玩的,沒做嚴謹調校,沒想到反響遠超預期。姚舜宇被測出 1000 萬美金的身價,其實還挺準的。
Aaron: 這個 AI 機器人具體是如何分層分析的?
高岱恆 Sam:用戶註冊後,我們會將其簡歷、社交媒體向量化。當你搜索時,系統會做意圖識別。比如你搜“頂會”,我們會自動映射到最近的 CVPR 或 NeurIPS。如果你找 00 後,Agent 會全網蒐集信息進行推理判斷。對於幾百人規模的論文作者列表,人肉篩選是不可能的,但 Agent 能瞬間根據重要性分級。
Aaron:那你們會不會有偏差,比如有些博士生做了重要工作但沒發出來,你們有沒有機制校正這種偏差?
高岱恆 Sam:問得特別好。這個我們後面會根據用戶問題去 index arXiv 的內容,但目前階段還沒有做到。
Aaron: 目前 B 端用戶的反饋如何?
高岱恆 Sam:Meta 負責高管搜尋(Executive Search)的團隊已經在用了,還有一些海外 AI 公司也在共建,他們需要極其立體的參考系。
孫辰昕 Kelvin:國內像 Flow、月之暗面、智譜、愛詩科技(PixVerse)等團隊都在低調試用。反饋最多的一個詞是“神奇”。 以前 HR 接到一個模糊的需求,那是極大的內耗;現在輸入需求,出來的候選人瞬間讓畫像變得具象化。HR 會驚呼:“原來這類人就是我要找的!”這種從模糊到清晰的飛躍,比單純找到人更有價值。
Aaron: 現在的客戶更傾向於招募有大廠經驗的資深科學家,還是更看重博士階段剛畢業的新秀?
孫辰昕 Kelvin:兩種需求都有,但目前偏向後者的更多。一方面,資深科學家非常昂貴;另一方面,那些處於“水面上”的名人,HR 基本也都認識。不過即便是面對熟人,我們的工具依然有價值:常有 HR 反饋,搜出來後才驚覺,“這人我加過微信,但早忘了”。畢竟人腦很難記住微信裡那 5000 個人。
Jane:這是否意味著在 AI 時代,招聘需求本身——尤其是高端人才的需求——發生了劇變,導致公司 HR 的原有認知已經無法覆蓋當下的技術邊界了?
孫辰昕 Kelvin:沒錯。你可以看看字節跳動是怎麼調整的:他們抽調了很多本身做算法、做產品、但可能在技術上沒那麼“頂尖”的員工去全職做招聘。因為這些人懂業務、懂技術,更容易找到對的人。
從目前的反饋看,字節 Seed 和 Flow 團隊的這種嘗試非常奏效。他們的高端招聘(高招)團隊裡有大量的人此前完全沒有招聘經驗,全是從業務線轉崗過來的。
但目前也只有大廠能用這麼奢侈的方式去解決。對於大多數公司來說,能招到這樣的人幹本行就不錯了,哪捨得讓他們去做招聘?這種“拿牛刀殺雞”的模式缺乏普遍意義。
Jane: 我記得以前認識一些獵頭,大公司如果想在北美找科學家,只能找那種深耕當地、認識很多科學家的獵頭。即便如此,人才畫像依然不明確,只能挨個拉人見面。整個過程極難標準化,本質上就是“廣撒網”。在需求端,這裡的變化確實是最大的。
孫辰昕 Kelvin:是的,事實就是如此。
這段對話涉及了產品的核心技術壁壘與用戶體驗細節。在不刪減任何內容的前提下,我主要優化了表達的連貫性,將口語中的零碎詞彙轉化為更具專業感的敘述,並強化了 Sam 邏輯中的技術高度。
Aaron: 我再深度理解一下:你們的產品是否會具體去閱讀 Paper(論文),以此來識別內容並匹配崗位?你們對人才畫像的標籤(Tag)能精準到什麼程度?
高岱恆 Sam:這種需求會自動觸發多個維度的匹配:首先是公開成果,比如像 Sora 2 這種有商業影響力的非開源成果;其次是 Hugging Face 上的熱門項目或高點贊成果;再往下就是那些處於“水下”的貢獻者,比如中山大學、蘇州大學等高校發表的論文。
目前為了兼顧效率,我們主要通過閱讀摘要來實現精準匹配。如果進行全文解析,Token 的消耗會極大,單人的處理成本也會隨之飆升,所以暫時沒有上線全文讀取功能。
Aaron: 你們目前接入了多少個數據源?
高岱恆 Sam:大約二三十個。Google Scholar、Medium、Twitter 等主流平臺都有覆蓋。arXiv 雖然還沒正式接入,但在計劃中。
Aaron: 頂會數據也做了預處理嗎?
高岱恆 Sam:頂會數據我們會提前處理。因為頂會發榜通常是一次性的,能直接獲取當年的會議名單和作者名錄。
Aaron: 從技術層面看,最難的環節在哪裡?是數據抓取、清洗對齊,還是隱私風控?
高岱恆 Sam:細節非常多,談不上“最難”,因為任何環節沒做好都會變成短板。我總結了三個代表性的挑戰:
1.消除歧義(Disambiguation):這在學術檢索領域是經典難題。現在重名的人太多了,如何確保不發生錯誤關聯至關重要;一旦關聯錯誤導致推錯人,用戶體驗會非常糟糕。
2.時效性:比如你想找的一位作者已經從 OpenAI 跳槽去了 Meta,但系統還顯示他在舊東家,這就是時效性問題。如何動態地更新數據庫並實時同步信息?傳統平臺最大的痛點就是扛不住被動更新帶來的成本。
3.Agent 路徑選擇:根據用戶需求,系統需要判斷去哪裡找、路徑怎麼縮到最短、向下鑽取多深。這涉及深度優先與廣度優先的交叉博弈。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持續對模型的閱讀理解(Read)能力進行升級。
Aaron: 針對第一點,能用更通俗的例子解釋嗎?比如區分兩個同名的 Yao Shunyu,他們的英文名也一致。
高岱恆 Sam:區分的標準主要有幾個維度:Google Scholar ID 的唯一性、照片的差異、教育背景以及職業發展軌跡(Career Trajectory)的不同。結合這些維度,就能精準拆開。
Aaron: 第二點關於更新,傳統做法是持續 Follow 對方動態,你們是如何捕捉實時更新的?
高岱恆 Sam:核心前提是互聯網上必須存在相關信息。這群技術人才很少使用領英,更多是維護個人主頁。但個人主頁極其分散,像 GitHub 獨立站這類,如果你不知道具體路徑就根本找不到。我們的優勢在於知道他們在哪裡,並預先對數據做了一層緩存,從複雜的獨立站中高效提取信息。
Aaron: 在實際運行中,有沒有遇到過比較 Tricky 或意想不到的案例?
高岱恆 Sam:有。前兩天我給朋友演示,問系統:“這位朋友的合作者中,哪些人可能在看機會?”結果反饋非常精準,而這位朋友本身是一位資深大學教授。還有一個我和蘇建林(蘇神)的案例:我想看我和他的合作關係有幾度。雖然我們沒直接合作過,系統卻能通過中間人順藤摸瓜找到關聯。
這說明了一個本質:當模型的智能化程度夠高、推理能力夠強、子頁面爬取能力足夠好時,“更少的結構化(Less Structure)”反而能帶來“更多的智能(More Intelligence)”。你可以更信任模型本身的判斷。
Aaron: 如果候選人沒有更新個人主頁,但在新發表的 Paper 裡備註了新機構或新公司,你們能捕捉到嗎?
高岱恆 Sam:可以。我們做的是全網信息聚合。即便本人沒更新主頁,我們也能通過他最新的學術軌跡捕捉到他的新動向。
Jane: 媒體新聞類的報道會作為你們的信息源嗎?
高岱恆 Sam:中心化媒體的信息往往存在滯後。目前我們更有效的信源是社交媒體,時效性更快。大型中心化媒體中,只有極少數會成為我們的輔助參考。
Aaron: 數據中不可避免涉及隱私,你們如何界定哪些數據可用於評估,哪些不能觸碰?
高岱恆 Sam:我們對隱私信息有嚴格界定。電話、微信號屬於“侵入式”聯繫方式,我們通常不提供。郵件相對屬於非侵入式。實際上,個人主頁上也很少有人留私人電話或微信,我們使用的絕大部分是公開可查的信息。
Aaron: 如果有人不希望在平臺上被搜到,你們怎麼處理?
高岱恆 Sam:只要有正式的申訴請求(Inquiry),我們就會把他的信息徹底從系統中刪除,確保不再出現。
Aaron: 使用 DINQ,你最喜歡的功能是什麼?
高岱恆 Sam:我最喜歡的是Network。當你查到一個人時,不只能看到他本人,還能看到與他合作最緊密的六個合作者。你可以點擊進入任何一個節點,再次看到以此人為核心的社交網絡。這意味著你可以通過一個點,順藤摸瓜地拉出一整套人才線索——包括論文合作、GitHub 貢獻、同公司小組關係等。它把找人從“單點搜索”變成了“網絡拓展”,在平臺上操作非常絲滑,點一下就能看到全貌。
Aaron: 我自己試用下來,覺得 Compare/PK(對比)功能也很有意思。
高岱恆 Sam:沒錯。PK 功能最開始做得比較抽象,像《拳皇》紅藍對打一樣。後來有朋友反饋,學術和開源圈的人未必覺得“Star 數少或引用低”就代表弱,大家會開玩笑說“你這純屬靠歲數大、不講武德”。所以我們現在的 PK 界面做得勢均力敵。這個功能的初衷是讓用戶在尋找人才的嚴肅過程中多一點趣味性,沒有太功利的目的。

李飛飛 vs. Jia Deng
市場與商業背後,AI 招聘的效率戰與價值戰
Aaron: 從市場角度看,你們的產品與傳統獵頭之間是什麼關係?是相互替代還是彼此輔助?
孫辰昕 Kelvin:短期內肯定是輔助關係。我們幫助招聘方大幅節約“搜尋(Sourcing)”環節的時間,但後續的深度溝通和說服工作依然需要人來完成。企業的選擇邏輯很簡單:有預算就外包給獵頭,沒預算就用工具自己做;遇到敏感崗位也會傾向於親力親為。目前我們扮演的是高效工具的角色。
長期來看,DINQ 會擠壓掉那些水平較低的獵頭。所謂“水平低”,是指在面對 AI 產品時連 Prompt(提示詞)都不會寫的人。我這兩天調研發現,真有獵頭連第一句需求都憋不出來,這類人在未來會非常危險。
Aaron: 能展開說說具體的成本賬嗎?獵頭怎麼收費,你們的商業模式又是如何交織的?
孫辰昕 Kelvin:以全球視野來看,頂級獵頭的收費通常是候選人年薪的 20%–30%。如果招募一個年薪 100 萬美金的高管,中介費就高達 20–30 萬美金。國內稍微低一點,但也普遍在 20%–25%。
我們的定價策略尚未最終敲定,但初步設想是每月一兩百到兩三百美金。即便是每天“捲到死”地在平臺上找人,一整年的成本也遠比請一次獵頭便宜。這筆賬,企業主一眼就能算清。
Aaron: 你們目前是將自己定位為“超級 AI 招聘助手”,還是未來的“AI 獵頭”?
孫辰昕 Kelvin:其實都不是。我認為 DINQ 是一個AI-Native 的人與人職場社交平臺。招聘只是職業社交的一種表現形式,此外還有找合作者、找客戶、找技術交流等海量需求。比如賣 API 的小公司需要找開發者客戶,做 AI 動效的設計師需要互相切磋。我們的視野絕不侷限於招聘。
我們的定位與早期的領英(LinkedIn)類似:更高效地展示自我,更高效地連接他人。至於連接後的行為是招募還是聊天,平臺都能承載。
高岱恆 Sam:補充一點,我們的思路是打造一個面向所有 AI 人才的平臺。ai-native 人才的定義是:用 AI 技術把自己的生產效率提升一個數量級。現在提升最多的是搞算法和開發的人,因為他們的生產力工具成熟;設計師工具也開始走向千家百戶。未來會有更多行業被改造,產生專用工具與工作模式。
這個時代去中心化,利好超級個體,但個體需要渠道去鏈接更好的機會和人。我們就是提供更好的鏈接與觸達。未來機會很多時候不是“人看到轉發給朋友”,而是 agent 自動去各類機會平臺分析,這一定會發生。它需要一個基礎載體。
所以我們讓 C 端上傳多種社交媒體來體現全面性:過去簡歷是給人看;AI 時代是給 AI 和人一起評價,主觀性、豐富性、不可被定義程度,都能通過照片、視頻、社交媒體體現。隨著模型對多模態理解提升,對人的刻畫會更立體。
從 2010 年微博、Twitter 把人打成 human-readable label,到今天用連續的 embedding 去勾勒人。未來個人發展的可能性、能力邊界某種程度也能被預測與規劃。這是平臺最大價值。day one 我們用核心技術吸引用戶,目前核心是匹配引擎,用引擎把人吸引上來。
孫辰昕 Kelvin:前陣子我們做了一次小規模投放測試,結果完全超出預期。
首先,職業廣泛性極高。入駐的不僅有宜家(IKEA)的首席科學家、Capital One 的首席 AI 工程師,還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個體。比如一位埃及女孩,她在 Twitter 上通過 AI 動效交付客戶;甚至還有一位填著“足球教練”標籤的埃及用戶,點進去發現他是利用 AI 進行數據訓練分析的教練。
其次,地域分佈極廣。雖然只是微調投放,但除了南北極,全世界的“邊邊角角”都有用戶。從非洲的埃及到中東、印度,再到丹麥、意大利,全世界都在為 AI “上頭”。這遠超我們最初認為只侷限在“灣區+海淀”的預期。
Aaron: 未來的商業模式是按 Credits(積分)、訂閱制,還是按結果付費?
孫辰昕 Kelvin:初步計劃以搜索 Credits 計費,保持簡單。C 端暫時免費,我們想等用戶規模上來後,觀察其行為和剛需點再定。B 端則採用類似 Agent 工具公司的模式,按 Credits 銷售。
Jane:有考慮過將 C 端做成社區型產品嗎?
高岱恆 Sam:產品形態本身就能承載社區功能。你可以把它理解為具有聊天功能的“AI 版 Linktree”。雖然現在還沒開放用戶發佈日常動態,因為新平臺初期這類內容的粘性不足。
Jane: 如果向投資人呈現 AI 招聘市場的 TAM,你們會如何描述?
孫辰昕 Kelvin:以前我們以為 AI 強相關從業者只有百萬級,現在發現AI Users(AI 使用者)才是更大的基本盤,全球範圍已過億。他們同樣需要在全球範圍內尋找合作與機會。平臺如果能讓這種極低概率的鏈接變得容易,空間是無窮的。
高岱恆 Sam:平臺的核心價值在於利用 AI 智能服務好用戶。我們會很快過渡到推薦模式:隨著我們越來越瞭解用戶,推薦會越來越精準。未來,用戶在這裡不僅能找合作者,還能找導師、找伴侶。
Jane:它是更長期的事情。短期 TOB,但長期天花板更高、更適應現在。
孫辰昕 Kelvin:對。而且我們真實業務也沒那麼 TOB/TOC,因為每個 B 也是一個 C 在工作,本質是一個真人在用,無非在工作場景用得更多。
高岱恆 Sam:我再往高提一點:平臺核心價值在於 AI 能幫助服務好用戶。傳統平臺是供給方與用戶共同創造價值;但今天像 ChatGPT,一個對話框也能成為平臺,因為大模型本身提供智能服務。我們也一樣:只要平臺智能足夠高、能解決足夠多問題,你就是一個輸入框,用戶也會來用。
我們會很快過渡到推薦模式。最開始我不瞭解用戶問題,上來就推人是瞎推。隨著我們越來越瞭解用戶,站內站外用戶交錯,推薦會越來越好、越來越準。
未來用戶不只是找合作者,還找導師、找伴侶。過去沒 AI 能力做不到最理性權衡:把所有可能適合你的導師都過一遍並評估,但信息佔有與處理效率太低。今天有引擎就可能做到。我們上線版本會有功能叫 find my adviser;找對象也是同樣邏輯。
孫辰昕 Kelvin:這不是開玩笑。大量人談戀愛結婚就是在工作場景認識的,是很真實的需求。也有人在領英上找對象。只要做得夠大,時間一到,它必然會出現。
Jane: 這確實很吸引投資機構。比如紅杉這種鼓勵內部創業的機構,如果能通過平臺點對點地直接聯繫到核心人才,需求會非常大。
孫辰昕 Kelvin:Exactly,是的。
Jane: 傳統領英團隊如果要復現你們的數據源和架構,門檻高嗎?
高岱恆 Sam:從架構上看,我們的異步搜索架構具備很強的競爭力。如果開源,拿 1 萬顆星不難。
復現一個版本可能只需要牛人花五個小時,但真正的壁壘在於錯誤判斷、路徑選擇以及長期的參數調優。因為在 AI 領域沒有標準答案,不懂業務邏輯的話,調優的過程會極其漫長。
Aaron: 近期大廠搶人非常兇猛,騰訊雙倍薪資挖人,阿里內部也在發力。你們怎麼看未來兩到三年的 AI 招聘市場?
高岱恆 Sam:一個明顯的趨勢是:除了塔尖的頂級人才外,中腰部人才的缺口其實更多。Indeed 首席經濟學家的數據顯示,美國目前缺口達 200 萬,重點在於 AI 應用層的人才,平均年薪 20.6 萬美元。
外界總在關注扎克伯格或張一鳴在挖誰,那些確實貴,但人數極少。更龐大的群體是那些開源貢獻者、小論文作者,以及小公司裡成果卓越的年輕人,他們的流動率更高。我們的核心策略和優勢在於:我們已經掌握了最頂尖的那波人,所以可以實現“從高往低”的降維打擊。
Jane: 你們測算過,全球範圍內大廠重金爭奪的這波頂尖人才大概有多少人?
高岱恆 Sam:全球大概在 10 萬到 30 萬這個量級。而且人才版圖正在飛速擴張:五年前主要是 CV(計算機視覺)和 NLP(自然語言處理),現在新增了具身智能、AI Agent、RAG、向量數據庫等諸多領域,崗位呈非線性增長。
Jane: 五到十年後,你們希望 DINQ 扮演什麼角色?
高岱恆 Sam:我希望五年後,每一位 AI 從業者都擁有一張DINQ Card,上面集成了他所有的技術渠道和社交標籤。他在平臺上不僅能找到機會,更能認識圈外的朋友,甚至找到志同道合的伴侶。我希望五年後的用戶規模能達到 1000 萬。
團隊、文化與「AI-native 公司」的組織設計
Jane: 你們團隊目前規模如何?
高岱恆 Sam:目前全職共 8 個人。
Jane: 你們有用自己的產品招人嗎?
孫辰昕 Kelvin:最近開始用了。我跟技術負責人開玩笑說,我最大的願望是明年能用 DINQ 招到全量人才。因為最初搜出來的人才級別太高,我們 offer 不起(笑)。
但令我驚喜的是,我們已經開始挖掘出一些“水下”的寶藏。我最近聊的一位增長負責人,就是從 DINQ 上發現並聯繫上的,這兩天剛加了微信準備深入交流。能從平臺上找到志同道合的人,這完全超出了我的預期。
高岱恆 Sam:搜索體驗非常直覺。比如你想找“在某某公司有過 GTM(去市場)經驗”的人,一兩句話就能出結果。
Jane: 只需要一兩句話?
高岱恆 Sam:對。用戶不需要像寫傳統 JD 那樣進行復雜的心理建設。在 DINQ,你可以沒有心理負擔,想到什麼就問什麼。
孫辰昕 Kelvin:以前寫 JD 很難,因為要求太高且需求模糊。用我們的工具,你可以先輸入一個大概的方向跑一跑。如果出來的人不對,你可以通過多輪對話不斷調優:比如“要更年輕一點”、“要更偏水下一點”。通過這種多輪 Narrow Down(縮小範圍),最後鎖定幾個目標直接聯繫。
Jane: 你們團隊文化的關鍵詞是什麼?這種文化如何映射到產品邏輯上?
孫辰昕 Kelvin:我覺得用“純粹”這個詞更貼切。
高岱恆 Sam:沒錯,純粹。我們這裡沒有亂七八糟的雜事,大家就像進工作室畫畫一樣,沒有死板的固定工時。這種純粹也體現在產品取捨上。比如評估身價的邏輯完全是我拍板定的;我們的搜索功能大方地展示 Network 和 Profile,而不是像某些產品那樣把候選人 Mask(掩蓋)掉逼用戶付錢。那種把人當資產、想方設法“加氣”的行為太小氣了。
我們追求的是 AI 時代的“全鏈路通暢(Fully Differentiable)”。當未來用戶規模達到幾十萬,你搜到人可以直接站內聯繫。
Jane: 你們的產品版式設計非常簡潔且高級。
高岱恆 Sam:這跟我學建築的經歷有關,我們對審美有品位。由於之前做過 AI 項目,我們知道用戶偏好什麼樣的視覺體驗。
Jane: 最後一個問題:對於現在年輕的 AI 學生或工程師,為了更有效地被大廠或同好發現,你們有什麼建議?
高岱恆 Sam:只有一句話:Building in Public。多寫博客、文章、代碼,分享你的觀點。我印象最深的是蘇建林(蘇神),他從初高中就開始寫博客,堅持了十幾年,才成為今天大家眼裡的“蘇神”。他的技術成了大模型的標準實踐。你要堅持得足夠久,才會有好的結果。不要執著於在公司做那些所謂的“保密大事”,真正好的東西一定要拿出來經受批判和評價。
孫辰昕 Kelvin:現在國內的變化也很快。小紅書上有很多科研人在分享日常、作品和會議,把“科研人生”寫活了。大家發現這些研究員也是有血有肉的小帥哥小美女,也養貓養狗。這些原來在水面之下的人,正通過社交媒體走到光亮處。
Jane: 確實,在小紅書上能看到像沈清紅老師這樣以前很少出現在社交媒體的技術大牛。那我們的今天的訪談就到此為止,謝謝兩位的時間。
歡迎加入深潮 TechFlow 官方社群
Telegram 訂閱群:https://t.me/TechFlowDaily
Twitter 官方帳號:https://x.com/TechFlowPost
Twitter 英文帳號:https://x.com/BlockFlow_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