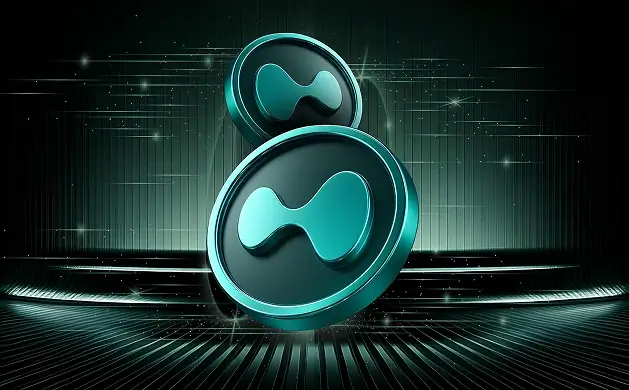“我不是罪犯” - SBF 獄中訪談:從加密帝國到孤獨審判
TechFlow Selected深潮精選

“我不是罪犯” - SBF 獄中訪談:從加密帝國到孤獨審判
“司法部可能覺得我是,但說實話,我並不在意他們的看法。”
整理 & 編譯:深潮TechFlow

嘉賓:Sam Bankman-Fried,FTX 創始人
主持人:Tucker Carlson
播客源:Tucker Carlson
原標題:Sam Bankman-Fried on Life in Prison With Diddy, and How Democrats Stole His Money and Betrayed Him
播出日期:2025年3月7日
要點總結
Sam Bankman-Fried 服刑 25 年,與 Diddy 同住一監區。Sam Bankman-Fried(SBF)正在監獄中服刑 25 年,他現在與 Diddy 共享一個監區。他從監獄中加入我們,分享關於他新生活的最新狀況。
訪談精彩觀點摘要
-
我不認為我是罪犯。我知道司法部可能覺得我是,但說實話,我並不在意他們的看法。
-
Gary Gensler 領導的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簡直是一場噩夢。
-
到 2022 年,我私下裡對共和黨的捐款已經和對民主黨的捐款持平。而巧合的是,這件事恰好在 FTX 崩潰前後被曝光了。
-
在我放棄對 FTX 的控制權之前,甚至在公司申請破產之前,司法部似乎就已經下定決心要採取行動了。
-
關鍵問題在於,當真正面對挑戰時,政府是否會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解決這些障礙。
-
我們國家的一些系統擁有巨大的權力,他們可以通過一些隱蔽的方式施加壓力和恐嚇,影響人們的決定。
-
他們沒有顯赫的背景,也沒有相關的經驗,卻能在公司裡表現得比幾乎所有人都好。這是因為他們有韌性、有直覺、有奉獻精神,懂得如何工作,如何與人合作,以及如何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
-
人們在不瞭解他人真實需求的情況下,憑空假設自己知道該怎麼幫忙,這種想法有時會顯得有些自以為是。事實上,許多外國援助項目最終完全浪費了資源,因為沒有人真正瞭解他們要幫助的人到底需要什麼。
-
如果行業能夠繼續專注於技術進步,而不是過於關注市場價格的波動,那麼在未來 5 到 10 年內,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輕鬆擁有一個加密錢包,數十億人每天都能通過它進行交易。這些交易將具備隱私性、安全性、快速且低成本,並且可以在全球範圍內無障礙完成。這些都是加密貨幣起初承諾的特性,但很遺憾,這些年行業的注意力被許多其他問題分散了。
監獄生活是什麼樣的?
Tucker:你在那兒多久了?那裡的生活怎麼樣?
SBF:
我在監獄裡大約有兩年了,這裡可以說有點像反烏托邦的感覺。幸運的是,我所在的地方並沒有身體上的危險。說實話,這裡的工作人員還是很努力地在幫助我們,他們儘量在有限的條件下做到最好,但沒有人會想待在這種地方。大約 40 個人被關在一個房間裡,這些人都因為某些罪行被起訴,幾年都無法離開。在這種環境下,哪怕是最小的事情,都會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
Tucker:你有遇到什麼麻煩嗎?
SBF:
不是那種暴力事件,我沒有被攻擊過什麼的,但我確實遇到了不少後勤上的問題。老實說,最大的困難是在審判期間,幾乎沒有機會處理我的法律事務。典型的審判日,我早上 4 點就被叫醒,然後花五個小時在各種公交車、麵包車和拘留室之間輾轉。庭審通常會持續到下午 5 點,然後我又得花四個小時在拘留室和麵包車裡折騰。等我晚上 9 點回到監獄時,基本上已經沒有時間再處理任何法律工作了。這是我面臨的最大問題。
Tucker:那麼,如果沒有審判,你平時都在幹什麼?
SBF:
這是個好問題,因為實際上沒什麼事情可做。我會讀書,重新開始看一些小說,偶爾下下國際象棋,儘量處理我的法律事務,比如上訴之類的。除此之外,我也儘量完成自己能做的工作。但監獄生活中最讓人難以忍受的,可能就是缺乏其他有意義的事情來消磨時間。
SBF 在入獄前是否服用過 Adderall?
Tucker:無論一個人被指控了什麼或做過什麼,我對每一個身陷囹圄的人都感到遺憾。我個人覺得,把人關起來並不是一個好辦法。
SBF: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或許有時候不得不這樣做,我也對每一個在監獄裡的人感到同情。這就是我的看法。你可以說我是個自由派。不過說實話,經過這兩年的監獄生活,我感覺你看起來比以前健康了,也沒那麼緊張了。
我在這裡有很多時間反思,尤其是關於溝通的問題。回想起來,我覺得自己在危機剛開始的時候,溝通做得並不好。那之後的一個月,我犯了一個老毛病,就是陷入了細節之中,卻忽略了全局。
Tucker:每次在電視上看到你時,你總是顯得很亢奮,像是吃了 Adderall 一樣。現在看起來你不是那樣了。你當時真的在用這種藥嗎?
(深潮 TechFlow 注:Adderall 是一種處方藥,主要用於治療注意缺陷多動障礙(ADHD)和嗜睡症,能幫助患者集中注意力提高效率)
SBF:
我沒有服用過。但我確實感覺當時腦子有些轉不過來,因為要處理的事情實在太多了。一般在 FTX 工作時,我常常一邊接受採訪,一邊還要處理公司的一些緊急事務。甚至在採訪時,我腦子裡還在想著其他問題,很多時候根本來不及準備,只能臨場應對。
Tucker:你怎麼看?現在你沒有手機了,這對你來說是不是很重要?
SBF:
我還是更喜歡有數字化工具的生活。說到底,這些東西對我來說不是為了娛樂,而是為了提高效率,以及讓我能夠對這個世界產生影響。從這個角度看,沒有數字工具,做任何事情都會變得非常困難。
SBF 在監獄中與 Diddy 的相遇
Tucker:在監獄裡你交到朋友了嗎?你和 Diddy 還在一個單元嗎?
SBF:
他確實在。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但他待人很友善。我也交到了一些朋友。這裡的環境很特殊,既有一些高調案件的當事人,也有很多前幫派成員或者被指控的嫌疑人。
Tucker:Diddy 是個什麼樣的人?
SBF:
說實話,我只見過他在監獄裡的樣子。他對我們單元裡的人都很友好,對我也不錯。不過,這種環境沒人會想待在這裡。他顯然也不想,我記得他提過,這種生活對所有人來說都像是一種靈魂上的壓迫。我們每天看到的只有身邊這些人,而不是外面的世界。
Tucker:你和 Diddy 可能是這裡最出名的兩個人了,生活在同一個單元。其他人,比如那些武裝搶劫犯,會怎麼看你們?
SBF:
這個問題很有意思。確實,有些人可能會覺得,哇,能認識我們這樣的人是個難得的機會。這我倒是有點意外,但我也能理解他們的想法。
我發現他們下棋特別厲害。這是我在這裡學到的一個有趣的事情。那些可能連初中都沒畢業、甚至不會說英語的前武裝搶劫犯,有不少人下棋下得相當不錯。我不是說他們是國際象棋大師,但每次和他們對弈的時候,我都沒想到會這麼有挑戰性。
SBF 自入獄以來的心態變化
Tucker:現在的情況怎麼樣?這些經歷有沒有改變你的看法?
SBF:
我覺得這是更大人生體驗中的一部分。這可能是我學到的最深刻的但仍未完全理解的道理之一。顯然智商、努力工作這些都很重要,但還有一些東西,我們似乎沒有合適的詞來形容。我也還沒有沒找到那個詞,但這些品質能讓一個人表現得極其優秀、成功、高效,甚至超越他人對他們的期望。當然,每個人的情況都不一樣。不過,在金融圈裡,我見過很多人,他們沒有顯赫的背景,也沒有相關的經驗,卻能在公司裡表現得比幾乎所有人都好。這是因為他們有韌性、有直覺、有奉獻精神,懂得如何工作,如何與人合作,以及如何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我以前在華爾街工作過,那裡真是臥虎藏龍,各種類型的人都有。
儘管捐款巨大,民主黨拒絕拯救 SBF
Tucker:
從整體來看,雖然我不想過多探討你的案件細節,但你們公司似乎通過政治捐款建立了政治關係網。這種做法很常見,你也不是唯一這麼做的商人。不過,你給民主黨捐了那麼多錢,我本以為他們會在關鍵時刻拉你一把,民主黨一向會保護自己人免於牢獄之災,為什麼你卻會有種遭遇?
SBF:
這是個很好的問題,但我也只能猜測,因為我並不知道他們真實的想法。不過,有一點可能相關:即使在 2020 年,我的立場還是偏中左的,我也為拜登的競選團隊捐過款。我當時對他能成為一個相對溫和的中左派總統抱有希望。但在接下來的幾年裡,我頻繁往返華盛頓特區,多次見人、開會,結果讓我非常失望。到 2022 年,我私下裡對共和黨的捐款已經和對民主黨的捐款持平。而巧合的是,這件事恰好在 FTX 崩潰前後被曝光了。
Tucker:是什麼讓你感到失望?我知道你在華盛頓待了很長時間,和幾乎所有人都見過面,還有很多合影流傳出來。到底是什麼讓你感到震驚?
SBF:
有些事情比我原本擔憂的情況更加糟糕。比如加密貨幣監管就是一個典型例子。我從沒指望民主黨會推動良好的金融監管,但我也沒想到他們會表現得如此糟糕。當然,每個黨派裡都有好人和壞人,也有一些深思熟慮的人。但 Gary Gensler 領導的證券交易委員會 (SEC) 簡直是一場噩夢。我看到的是,一家公司在美國提供某些服務時,Gensler 就會以“未註冊”為由對他們提起訴訟。Gensler 一邊說歡迎註冊,但實際上卻沒有明確的註冊流程。幾乎所有的加密貨幣項目都遇到了這個問題,沒有一個能成功註冊。這是我覺得非常令人不安的地方。
Tucker:你能解釋得更清楚一點嗎?像我這樣的外行人看來,Gary Gensler 顯然很腐敗,這一點毋庸置疑。但他的動機是什麼?他到底想要什麼?
SBF:
這是個好問題。我無法揣測他的內心想法,但我有一些猜測。他似乎非常喜歡掌控權力的位置。權力是很多人追求的東西,他也不例外。這可能更多是為了擴大他的權力範圍,他希望他的機構能掌握更多的權力,即使他並不打算用這些權力去推動行業發展,而只是阻礙行業前進。我不明白的是,他為什麼一邊強制要求所有人註冊,一邊又不給出明確的註冊指引。即使他自己也不知道如何處理這些註冊的公司。
Tucker:聽起來,這種行為和華盛頓的風格非常吻合。我以前也見過類似的情況。
SBF:
這並不是道德層面的問題。他並不是那種有強烈共產主義信仰的人。
Tucker:
當事情開始惡化時,你被指控犯罪,或者可能面臨指控。按常理來說,一個捐了那麼多錢給民主黨的人,通常會給他們的支持對象打電話求助,比如說:“嘿,我遇到麻煩了,你能幫幫我嗎?”你有沒有給舒默或者其他你支持過的人打電話,請求他們幫忙,比如讓拜登政府的司法部對你網開一面?
SBF:
我沒有,這有幾個原因。首先,我不想做不合適的事情。其次,很多人很快就表明了態度,與我劃清了界限。到那個時候,我和華盛頓的共和黨人之間的關係可能比和民主黨人更好,儘管這不是公開的,但從外部來看應該不難察覺。
最後,這裡還有一個複雜的故事,涉及一家在案件中扮演了特殊角色的律師事務所。但實際上,在我放棄對 FTX 的控制權之前,甚至在公司申請破產之前,司法部似乎就已經下定決心要採取行動了。
唐納德·特朗普執政下加密貨幣的未來
Tucker:你怎麼看加密貨幣的未來?你覺得加密貨幣的發展速度如何?它們現在是在朝著理想的方向前進嗎?
SBF:
希望是這樣吧。你看看特朗普政府剛上臺時的表態,其中有不少積極的內容,也有很多與拜登政府截然不同的政策方向。當然,關鍵還是在於後續的實際行動,而我們現在正處於這個關鍵階段,等待看會發生什麼。不出意料,政府換屆確實有助於改變局面,但金融監管機構是聯邦政府中龐大的官僚體系,通常反應遲緩。在過去十年裡,這些機構在加密貨幣領域更多扮演的是“阻礙者”的角色。美國的加密貨幣市場只佔全球的 5%,但美國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卻佔 30%。這種不匹配完全是因為監管問題。美國的監管環境在全球範圍內非常獨特。因此,我認為關鍵問題在於,當真正面對挑戰時,政府是否會採取必要的措施來解決這些障礙。
Tucker:
我記得加密貨幣剛進入公眾視野時,它被宣傳為一種可以恢復個人商業自由的貨幣。它承諾讓人們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自由買賣,同時還能保護隱私。但顯然,這種願景並沒有實現,看起來也不太可能實現。我現在幾乎聽不到有人再提隱私問題,加密貨幣似乎成了另一種資產投機工具。那麼,現在隱私問題的狀況如何?
SBF:
其實,加密貨幣不僅僅是投資工具,它在技術層面上也有很多實際用途,比如跨境匯款和支付。只不過,這些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通常需要更長的時間。相比之下,投資泡沫的起伏則顯得頻繁得多,幾乎每天或每月都會發生。
目前,加密貨幣還沒有發展到可以成為全球四分之一人口日常工具的程度。目標雖然還沒達成,但也已經不遠了。如果行業能夠繼續專注於技術進步,而不是過於關注市場價格的波動,那麼在未來 5 到 10 年內,我們或許可以看到一個全新的世界,任何人都可以輕鬆擁有一個加密錢包,數十億人每天都能通過它進行交易。這些交易將具備隱私性、安全性、快速且低成本,並且可以在全球範圍內無障礙完成。這些都是加密貨幣起初承諾的特性,但很遺憾,這些年行業的注意力被許多其他問題分散了。
Tucker:你覺得各國政府會允許這種情況發生嗎?如果真的允許全球人口進行不受政府控制的金融交易,那豈不是會動搖政府的根基?
SBF:
關於政府對金融交易的監管程度,不同國家的態度差異很大。以比特幣為例,雖然錢包是匿名的,但每一筆交易都會記錄在公共賬本上,任何人都可以查詢。因此,即使政府不直接控制這些交易,他們仍然可以通過公共賬本獲取一定程度的信息。
不過,並不是所有國家的政府對這種透明度持相同看法。在過去 30 年裡,美國政府對金融交易的控制有著非常明確的立場。法國等其他國家在這方面也採取了類似的態度,尤其是在涉及國際貨幣交易時。相比之下,一些更具威權色彩的國家可能會採取完全不同的策略。但實際上,全球有一半的國家並沒有像美國那樣試圖對日常金融交易進行如此深度的干預。
SBF 還剩下任何錢嗎?
Tucker:在這一切之後,你手上還有錢嗎?
SBF:
基本上沒有了。我之前的公司現在還在破產程序中。我不確定具體情況。如果沒有其他干預的話,公司目前的負債大約是 150 億美元,而資產大約是 930 億美元。
所以,理論上說,答案應該是有。也就是說,理論上有足夠的資產來償還所有債務,甚至還能支付不少利息,給投資者留下數十億美元的盈餘。但現實是,事情並沒有按計劃發展。公司的資產在破產程序中迅速流失,那些接管公司的人把數十億美元的資產轉移了出去。這是一個巨大的災難,未能阻止這一切發生是我這一生中最大的遺憾。
Tucker:在被指控之前,你是這個行業最知名的人之一。你覺得自己是加密行業裡最大的罪犯嗎?
SBF:
我不認為我是罪犯。我知道司法部可能覺得我是,但說實話,我並不在意他們的看法。
Tucker:
你現在身陷囹圄,這顯然說明他們是這麼認為的。不過我想問的是,你認為加密行業裡存在很多陰暗的行為嗎?
SBF:
確實如此。十年前,這種現象尤其明顯,或者至少相對於當時行業的規模來說是這樣。回看 2014 年到 2017 年那段時間,加密行業的規模遠不如今天。我見過很多交易,其中相當一部分交易的用途,嗯,用不同的話來說,就是“灰色地帶”。比如,“絲綢之路”就是一個典型案例。十年前,人們使用加密貨幣在網上購買毒品是很常見的用途。
當然,任何行業中都會有犯罪分子存在。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行為在加密行業中的比例顯著下降。一方面是因為加密領域的其他合法用途逐漸增多,另一方面也因為政府加強了反洗錢 (AML) 方面的監管。所以,現在雖然仍然存在一些陰暗行為,但它們已經不像早期那樣普遍了。
Tucker 質問 SBF 關於“有效利他主義”
Tucker: 你曾經被認為是“有效利他主義”這一理念的代表人物。這種世界觀或意識形態,甚至可以說是一種信仰,核心理念就是追求為最大多數人帶來最大福祉。你賺錢的目的據說是為了幫助儘可能多的人。然而有人指出,隨著你公司的崩潰,大約有 100 萬人因此失去了他們的資金。這似乎帶有一種諷刺意味,因為你一直倡導的理念就是為最大多數人帶來善意。
我想知道,這一切是否讓你重新審視有效利他主義的理念?
SBF:
我並沒有重新審視這些原則。顯然,我對發生的事情感到非常糟糕,這完全不是我所期望的結果。我知道,如果事情順利進行,結果可能會截然不同。人們本可以收回他們的錢,但等待的過程對他們來說過於煎熬,而且他們最終拿回的只是美元,而不是其他實際的價值。此外,我曾希望通過公司為世界做出的一切好事,也幾乎都因為公司的崩潰而被削弱了,甚至可以說是徹底被摧毀了。
Tucker:我想大多數人很難理解,幫助那些從未見過的人比幫助身邊的人更有價值或更具道德意義。換句話說,幫助你的親人或朋友,可能比幫助一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更顯得有意義。我想大多數人直覺上是這樣想的,而你似乎並不同意。
SBF:
我確實不同意,但前提是要避免一個常見的錯誤。很多時候,人們在不瞭解他人真實需求的情況下,憑空假設自己知道該怎麼幫忙,這種想法有時會顯得有些自以為是。事實上,許多外國援助項目最終完全浪費了資源,因為沒有人真正瞭解他們要幫助的人到底需要什麼。比如,有些團隊可能會帶著一堆水泵去一個水源充足但缺乏食物的地方,這樣的援助顯然是毫無意義的。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當你幫助熟悉的人時,你會更瞭解他們的需求,這確實是一個優勢。即使我認為每個人的生命都是同等重要的,這並不意味著我幫助一個陌生人的效果會和幫助熟悉的人一樣好。
Tucker:但我覺得你剛才的回答其實是在反駁有效利他主義的觀點。我的意思是,有效利他主義的邏輯看起來太簡單了。比如,治癒小兒麻痺症可能相對簡單,但讓一個人 30 年內都保持快樂卻非常困難。所以,也許那些更復雜、更困難的事情才更值得去做。
SBF:
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想舉瘧疾作為一個例子。在美國,幾乎沒有人因為瘧疾而喪命了,但全球每年仍有大約 100 萬人死於瘧疾。這是一種本不該再奪走人們生命的疾病。我們知道如何從理論上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去行動。雖然解決瘧疾在某種程度上看起來很簡單,但這並不應該成為我們忽視它的理由。
許多最貧困地區的干預成本其實並不高。如果我們能夠高效地分配資源,這些努力不會顯著影響我們國內的援助預算。但關鍵在於效率。如果我們把資源浪費在那些不需要幫助的地方,比如向缺乏食物的村莊提供無用的水泵,那就無法真正挽救任何生命。
Tucker:
你說的確實有道理,這顯然是事實。過去 60 年對非洲的援助中,許多地方的生活預期反而下降了。但從道德角度來說,當你的親人正面臨抑鬱或其他問題時,如何能證明優先關心瘧疾患者是合理的?難道不應該先幫助身邊的人嗎?
SBF:
如果我能做到的話,我當然會這麼做。但歸根結底,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責任。如果我很瞭解我的親人,並且知道如何幫助他們,那麼我當然有責任去解決他們的問題。但如果我已經盡力了卻無能為力,而與此同時我能夠通過其他方式拯救更多的生命,我不認為這會削弱我在國際上所能做的善行。
Tucker:最後一個問題,你能想到最近一個毫無疑問成功的國際援助項目嗎?
SBF:
當然有一些,但我不會具體說出名字。需要說明的是,這些並不是政府主導的項目,而是一些私人資助的項目。比如瘧疾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通過主要由私人捐助推動的努力,全球許多地區的瘧疾病例已經顯著減少,尤其是在非洲和印度,每年挽救了數十萬人的生命。平均而言,每挽救一條生命的成本大約是幾千美元,這在相對規模上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案例。
我們談的不是數萬億美元,而是幾十億美元的資金,這些資金通過精心規劃得到了高效分配。當然,如果你看一些政府主導的項目,可能會發現它們的效果微乎其微。如果你想了解政府成功的案例,比如馬歇爾計劃,它在二戰後重建德國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SBF 是否會真正出獄?
Tucker:如果你沒有被赦免,假設一切都保持不變,你出獄時會多大年紀?
SBF:
這是一個複雜的計算。我並不完全理解所有細節,因為涉及到第一步法案的內容。如果你簡單地把我的監禁時間和年齡相加,那麼答案是我會在四十多歲的時候出獄。
Tucker:你能應對那樣的生活嗎?
SBF:
抱歉,我剛才說錯了。如果考慮到我的監禁時間和年齡,出獄時可能是在五十多歲。如果包括所有可能的減刑,可能會在四十多歲。但我當時 32 歲被定罪,判了 25 年的刑期,那就是 57 歲。
Tucker:那麼,考慮到你已經服刑兩年,你認為自己能撐得住嗎?
SBF:
老實說,我也不確定。最難熬的部分是這裡沒有什麼有意義的事情可以做。據一些研究顯示(雖然我不確定其準確性),監獄的自殺率據說是普通社會的三倍。所以,想象一下,我的 25 年刑期乘以三,再加上我被定罪時是 32 歲,這種計算結果確實讓我感到很壓抑。
Tucker:從一個數字貨幣的世界轉變到一個完全沒有金錢的世界,這種反差真的很奇怪。監獄裡大家用什麼作為交換媒介?
SBF:
在監獄裡,大家用手頭能找到的小物品作為交換媒介,比如塑料包裝的鬆餅。這種鬆餅可能已經在室溫下放了一週,通常是你在加油站櫃檯上能看到的那種。除此之外,還有方便麵或者油封魚罐頭,雖然看起來很噁心,但它們在這裡都能派上用場。
Tucker:所以你從加密貨幣的世界轉到了鬆餅經濟的世界。你怎麼看待這兩者?畢竟,國際間轉移鬆餅顯然要困難得多吧。
SBF:
沒錯,我覺得鬆餅作為一種貨幣顯然不會成為全球的戰略儲備。它們的價值完全基於需求,沒有其他附加價值。雖然鬆餅的可替代性不高,但也算差不多。兩塊鬆餅大致相似,所以可以互相交換。但這種貨幣體系只能支持小額交易,比如五美元以下的交易。如果你想用鬆餅完成 200 美元的交易,那就很難實現了。
在監獄裡,一切交易的規模都非常小。你甚至會看到有人為了一個香蕉打架,但這並不是真的因為他們特別喜歡香蕉,而是因為他們沒有其他方式來發洩情緒。
為什麼 SBF 的朋友、家人和同事都拋棄了他?
Tucker:自從你入獄以來,你面臨著最高 23 年的刑期。我很好奇那些曾經受過你幫助的人,尤其是華盛頓的那些人,有沒有給你打電話,表達關心或祝你好運? SBF:
在公司崩潰後的最初階段,我確實收到了不少人的問候,包括一些來自華盛頓的朋友。但大約六個月後,這些聯繫就逐漸消失了。到了審判階段,幾乎沒有人再主動聯繫我。整個事情變得高度政治化,風險太高,沒人願意冒險跟我保持聯繫。
Tucker:真的沒有人聯繫你嗎?我注意到你的前女友在法庭上作證反對你。有沒有朋友仍然對你保持忠誠?
SBF:
有,但非常少。這讓我感到很意外。不過仔細想想,這也可以理解。任何與我親近的人都會面臨巨大的壓力,他們不得不做出選擇,而其中一種選擇可能會讓他們自己也面臨幾十年的牢獄之災。比如,Ryan Salem 的經歷就是一個非常悲慘的例子。他被指控犯下一些完全虛假的罪名。
他本來拒絕認罪,但檢方卻威脅他的妻子,甚至說如果他不認罪,就會把他的妻子也送進監獄。最終,他為了保護妻子,不得不選擇認罪。這種行為在法律上根本不應該被允許。
這種行為完全背離了正義的原則,讓人無法信任,他是一個好人,他沒有做錯任何事情。
Tucker:你有沒有意識到外面的世界變化得非常快?等你出獄時,可能會發現自己置身於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SBF:
是的,我確實有這種感覺。世界在不斷髮展,而我卻被困在原地,無法跟上它的腳步。
Tucker:生孩子是你“有效利他主義”哲學的一部分嗎?
SBF:
不是。對於這個問題,社區中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在過去五年裡,我感覺自己就像有 300 個孩子一樣,因為我的員工們讓我感到肩上責任重大。我幾乎沒有時間去關注個人生活。
Tucker:那些員工有沒有來看過你?
SBF:
沒有,幾乎沒有人來,只有一兩個人。
Tucker:或許你應該考慮有自己的孩子。因為當你陷入困境時,他們會一直陪伴在你身邊。
SBF:
這件事確實讓我思考了很多關於信任和依賴的問題。我們國家的一些系統擁有巨大的權力,他們可以通過一些隱蔽的方式施加壓力和恐嚇,影響人們的決定。
歡迎加入深潮 TechFlow 官方社群
Telegram 訂閱群:https://t.me/TechFlowDaily
Twitter 官方帳號:https://x.com/TechFlowPost
Twitter 英文帳號:https://x.com/BlockFlow_News